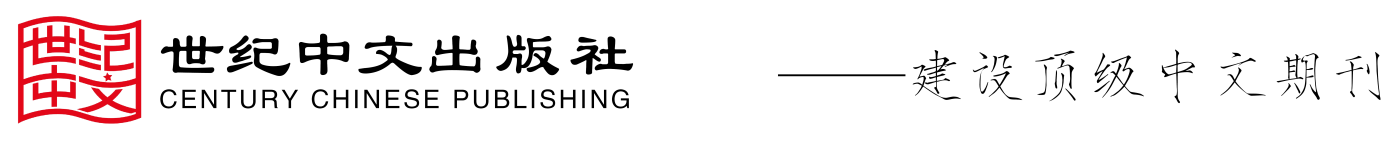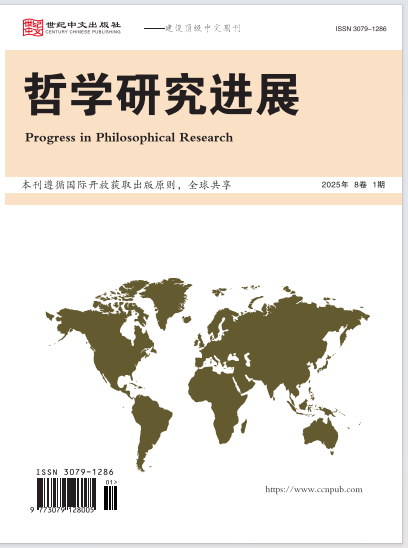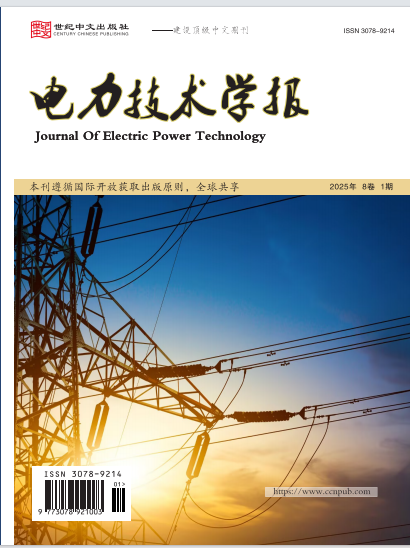以往学界对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的分析主要是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出发的,从而忽视了对黑格尔内部国家制度的批判研究,但该部分内容恰恰对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转变及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重新思考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内部国家制度,即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批判。
一、对黑格尔王权理论的彻底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王权理论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黑格尔完全弄混了普遍性前提与具有特殊性的个体的关系,应始终坚持从现实的人出发来寻找一切东西的现实普遍性,并提出“人民主权”论来否定黑格尔所坚持的“君主主权”论。
首先,就王权的规定上,即黑格尔的“王权即任意”观点,马克思就给予了激烈批判。前者认为“整体的绝对性环节就不是一般的个体性”,而在于个人,这个个人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而是君主。国家主权掌握于君主手中,只有在君主这一单一个体中国家主权才能拥有实体性的存在,才能在现实中有其载体并发挥自己的作用。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此处有一个“逻辑在先”的规定,即国家主权这一可被称为“人格”的东西先于使“人格”的现实性得以实现的“人”而存在,这里的“人”可指“君主”。那么从黑格尔的这一精神的外在规定和逻辑出发,“人格”先于“人”存在,作为分有具有人格的“市民社会”与“家庭”的主体即国家,必然不可能是单一个体的权力代表,国家主权也必然不会仅仅是单一个体权力的显现,不可能是君主个体的意志,而是多个个体自由意志的集合。黑格尔这一只有在某个单一个体中才能实现的“王权”就与其“市民社会、家庭”与“国家”的关系的逻辑相矛盾了。马克思在此指出,对于国家主权的规定应当从现实经验生活与组织方式出发,现实的人先于作为人的形式规定的人格而存在,国家人格是国家各个个体自由意志的集合体现,而非君主单个个体的权利。
其次,马克思就批判“主权在君”思想指出,国家人格是国家个体的意志集合体,是人民的权力。黑格尔坚持君主制,在君主的产生上,这一过程是先天决定的,具有明显的肉体偶然性;在君主的权力使用上,君主的最后决断具有极大的任意性,具有意志的偶然性。我们可知,国家是普遍伦理精神的外化,它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遍性本质,但在“王权即任意”理论中黑格尔又认为君主具有“肉身偶然”与“行为偶然”的偶然性特质,二者虽然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实现了普遍性对特殊性的完美统摄,但在现实的经验生活中却是自相矛盾的。马克思坚定反对“主权君主”理论,他指出国家主权是人民的共同意志,以此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民主制间接赋予国家主权以普遍性本质,国家主权的普遍性不再是黑格尔所提的以一种精神的外在规定来实现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地内在地存在于国家中各个个体之中的。
二、对黑格尔行政权思想的批判
马克思对行政权也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并阐述了自己的官僚政治思想。黑格尔认为,行政权是使得各个特殊领域和个体事件,如市民社会及其事务等从属于普遍物的权力。在行政权中,黑格尔还设置了警察权与司法权,以此来共同完成协调普遍利益的任务。行政权所体现的官僚政治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调和市民社会中的利益冲突,维护全体利益并使之服从于国家普遍利益的“政治工具”。官僚机构具有“刚正不阿”的性质,但黑格尔仅仅只是对其在“形式”的组织上进行了简单的规定。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官僚政治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等级制以及神秘主义特征,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形式主义”。官僚机构在形式上完成着自己的任务,但由于其组成人员具有一定的等级特质,逐渐形成自己的特殊利益,它原本代表普遍利益精神逐渐被物质利益精神所取代,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寻找各种方式来虚构自己的普遍性与公共性以此证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如意志万能论。马克思还指出,黑格尔的官僚政治无论是在官僚选拔,还是机构的监督中都具有背离黑格尔原初设想的私利性质,究其原因在于等级制及其私人利益的维护,而解决方法在于寻找到一个真正的能代表普遍利益的阶级,而不是黑格尔官僚机构这一普遍利益的虚幻体现。马克思在其思想后期有提出摒弃官僚政治就在于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公有制的相关观点。
三、对黑格尔立法权思想的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立法权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立法权与国家制度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认为立法权从属于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立法权的前提。黑格尔的“国家制度”与“国家”产生的逻辑相同,都是精神的现实化体现。国家是理念的自我运动,而国家制度是理念的实现。因而,国家制度是独立于一切事物,它不以其他事物的意志而转移,它决定着立法权。他也承认,国家制度是通过立法权、法律等手段使得自身不断发展并逐渐完善着的。马克思则指出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国家制度与立法权的矛盾问题,他只是站在普鲁士王国的立场上来维护君主专制,不愿让群众认识到立法权拥有制约国家制度、制约王权的作用。真正的可用于解决国家制度与立法权的矛盾的方法在于将人民视为政治国家的原则,即人民是立法的主体,立法权是人民自由意志的最高表达方式,人民拥有制定国家制度的权力,且可随时代与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来逐渐完善国家制度。
其次,马克思有力地批判了黑格尔在立法方式上采用具有等级性的代议制,但在立法主体上却以“等级要素”或市民社会成员的立法意见的单一性、私人性以及特殊性和立法是解决国家普遍事物的目的相矛盾的观点。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立法中纳入“等级要素”即市民社会这一私人等级不过是“形式上”的规定,“只是为了迎合逻辑”。马克思主张在立法主体与方式上要真正地将全体人民纳入立法的过程中来,全体人民都有权参与立法,不能如黑格尔所言去除“等级要素”,应当采取“全体人员都单个地”直接参与的方式。
最后,马克思在提出他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中丰富了自身,论述了“私有财产决定国家制度与法”的观点。他认为私有财产即长子继承权规定着国家制度与法,而非该制度是政治的要求。若要寻找证明私有财产决定国家制度以及立法权的证据,该制度本身即为最有力的论据。
结 语
综上,无论是对王权的规定,还是行政权与立法权的相关理论,从根本上而言都是在探讨具有普遍性的国家与具有特殊性的人民之间的问题,尤其是国家的普遍性的来源。黑格尔认为它是先天的存在,规定其他一切事物,而马克思坚持从现实的人出发,人民的事务才是普遍性的事务。
参考文献
[1]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龙佳解,罗泽荣. 论马克思的国家批判理论及其价值旨趣[J]. 理论学刊,2013(11).
[4]赵敦华. 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和马克思的批判[J]. 哲学研究,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