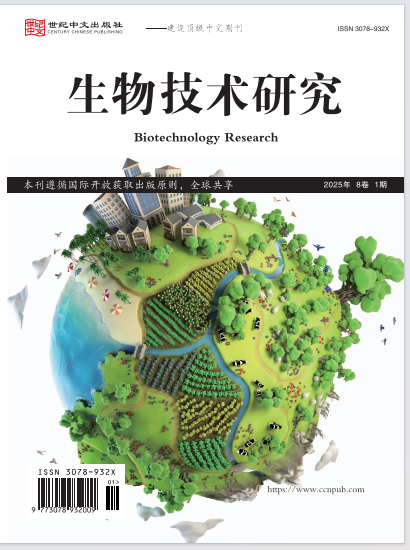1前言
1.1国内外湖泊水库现状及问题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废水的处理成为重要的问题。当下,废水和生活污水相互混杂,使得下水道管网长期失修,导致河流流动性差,水体富营养化、黑臭、藻类爆发等问题日益严重[1]。频繁的水华导致藻类毒素的释放,大大增加了水的耗氧量,破坏了水的功能,诸多水生植物遭受灭顶之灾,导致水体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以蓝藻细菌为例,铜绿微囊藻产生的胞内代谢物导致卵变异、水生植物如鱼类和水生跳蚤等死亡或生长出现问题。甚至影响水源的供水安全,从而影响人类的健康。
湖泊和水库的富营养化问题一直是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营养物质包括氮磷元素等,并且难以判断其来源。就当下的研究看,点源和面源污染是水体富营养化状态形成的最主要机制。除此之外,在水生态系统的富营养化状态形成的过程中,有毒藻华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尚且没有被实验证明。但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蓝藻藻华能够促进湖泊的富营养化进程。富营养化引起的蓝藻水华是湖泊和水库生态系统受损的主要特征之一[2-5]。
1.2藻类常见处理方法与问题
当下已经投入广泛使用的除藻技术包括化学、物理和生物技术。物理学通常是由空气浮选、遮光、微过滤、吸附等物理方法去除水中藻类,但藻类会引起滤床堵塞,如滤床堵塞导致工作量大,周期时间和成本较高,所以只有对小地方水域或大型机构的水[6]。
由于藻类密度较小,通常不易沉淀,因此可以借助气浮法使漂浮在水中的藻类迅速浮起至水面,从而实现高效的除藻效果。然而,这一技术也有其弊端。气浮池附近的气味较大,并且藻渣难以得到妥善处理。此外,气浮工艺很容易受到藻类的浮沉调节机制的影响。而化学除藻法则是使用化学药剂对藻类加以清除,也是目前国内外应用最广泛、相对成熟的除藻技术。包括混凝除藻,预氧化除藻,臭氧除藻,光催化除藻等,但由于其对非靶生物的杀伤作用,影响水生生态系统的安全,加速藻类毒素的释放,造成二次污染,其开发应用受到限制。
利用自然界中的生物或者人工培养的生物对水体中的藻类进行去除的方法即生物除藻技术,这种技术是恢复水环境健康的一种方法。采用该方法控制藻类具有安全、成本低、无二次污染等优点,但也存在杀藻周期长、杀藻率较低的缺点。生物除藻包括微生物除藻,生物膜除藻,水生植物除藻等方法。本文从微生物除藻,生物膜除藻,水生植物除藻技术等方面论述了生物法除藻在藻类防治中的研究,综述了国内外的生物控藻技术,为生物控藻技术在藻类防治中的应用提供参考[7]。
2生物法除藻
2.1微生物除藻
在藻类繁衍和毒物产生的过程中,水体内的微生物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例如,黏菌类的微生物、蓝藻噬菌体以及部分真菌等能够对藻类的细胞结构进行破坏,或者对其细胞营养机制进行破坏。有研究证明,将诸多细菌如放线菌、酵母菌等按一定比例混匀并培养后能够有效降低水体中的叶绿素a、氮磷元素和COD的含量,因此能够对解决水体富营养化产生裨益。实验结论表明,微生物群落可以对水体中的富营养化情况加以控制。
近年来,微生物除藻技术展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因此逐渐得以广泛应用。例如,日本北海道松前郡观音桥川、绿川河和鸟取县松江市掘川河等曾发生过严重富营养化的水体已经使用微生物除藻技术进行除藻,并且菌群投放后效果显著。而在我国,广西南宁等地区的除藻试验也取得了突出进展。
然而,就现有的研究结果看,导致藻类过度繁殖的机制尚且难以明确。虽然氮磷元素和COD指数均有所下降,并且这一现象可能与微生物区系减少相关,但与之相反的是,BOD指数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并且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解释方法,推测可能和有效菌群的增殖相关[8]。
将能够抑制藻类增殖或杀灭藻类的细菌称为溶藻菌。在水体生态系统中,细菌的作用不容小觑,因为其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藻类的生物量的平衡[9]。现有研究表明,溶藻菌的感染可能导致了赤潮与水华的突然消失。虽然传统的物理化学除藻技术存在着诸多限制,但生物除藻技术却表现出了难以预测的优越性。溶藻微生物大多从赤潮或水华的既往发生点分离得到[10]。在生物除藻技术的研究领域,溶藻菌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关注焦点。已经得到研究证实的溶藻菌[11]包括交替假单胞菌(Alteromonassp)、黄杆菌属(Flavobacteriumsp)、嗜胞菌属(Cytophagasp)腐生螺旋体属(Saprospirasp) 和黏细菌属(Myxobactersp )等,这些细菌的革兰染色大多为阴性,并且数量相对广泛。有学者[12]为探索固定化溶藻菌处理富营养化水体的成效,制作了动态膜生物反应器,并在膜组件中放置了溶藻菌RZ14菌株。在实验过程中,对水体中的有机质、氮磷元素和叶绿素a等指标进行了跟踪监测,发现COD的去除率为50.08%,而BOD的去除率则高达71.24%,氮磷去除率则分别达到70.73%和86.79%。事实证明,这种生物除藻技术能够迅速改变水体的富营养化状态,因此其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除了溶藻菌之外,病毒Cyphage也能够对蓝藻和水华进行控制。澳大利亚莫尔顿湾的藻类灭绝事件可能与之有关[13]。有学者进行了关于此类病毒的相关试验,发现感染病毒的蓝藻细胞在数天的时间内逐渐溶解,而真核生物群落中,轮虫成为了优势种群。这项研究证实了病毒在碳循环通路中发挥的作用,并且提示其控藻机制可能与改变真核生物群落的能力有关。此外,另有学者对富营养化的水体中的铜绿微囊藻和蓝藻噬菌体的密度进行了检测,并且发现当前者群落有所减少时,后者的密度会突然增加。此外,病毒与蓝藻宿主细胞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证实。病毒细胞裂解的过程能够造成蓝藻细胞的死亡[14]。
2.2生物膜除藻
原位生物膜技术可以有效控制处理水中藻类的含量,其控制机理主要是生物絮凝和微生物对藻类的分解。填料上的大量微生物和分解的化感物质可以抑制水源内藻类的生长,进而抑制水华的发生,有利于水源水质的恢复。在水体生态系统中,生长中的藻类能够起到化学调节剂的作用,这是因为它能够吸收水体中富余的氮磷元素。生长在藻类栖息地的营养物较多的浮游植物即栖息地,而营养物则更集中于此,故而浮游藻类的生命代谢活动远不如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藻类,例如附着的藻类和沉积物之间存在着空隙,并且水体中的营养成分密度远高于沉积物表面的游离水[15]。
有学者[16]采取了原位生物膜的技术,将除藻率提升至80%,并且发现除藻率和水力停留的时间呈正相关。实验结果提示,水力停留的最适时间为5小时。为进一步提升除藻率,可以将高锰酸钾与生物膜进行复合,借助高锰酸钾的氧化作用促进除藻率的进一步提升。原位生物膜法能够有效去除氮磷元素和有机物,并且能够将去除率保持在40-80%之间。
另有学者[17]使用最佳HRT和气水比对含有高浓度藻类的水体(叶绿素a =70 mg/m3)进行去除,发现叶绿素a、COD和氮磷元素的去除率可以达到65.48%、47.81%和70.54%,处理结束后的水体的氨氮浓度则为出水氨氮浓度分别为4.40 mg/L和0.40 mg/L,符合相关标准。本实验得出结论,即在藻类浓度发生变化时,最优HRT和气水比能够作为有效的应急处理方法,且效果相对良好。
生长于水体基质表面的藻类被称为附生藻类,其生长需求与浮游藻类相似,并且同样依靠水中的氮磷元素生存。由生态竞争排斥原则可以推断,可以借助这一原则构建浮游藻类和附着藻类之间的竞争模型,从而实现对浮游藻类生物群落的有效控制。
网藻的结构类似网袋,其细胞构造相对简单,每个网袋中含有4-6个细胞。这些网藻的生存地点为沟渠和池塘等地。日本科学家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相比蓝藻和绿藻,水藻具有更强的繁殖能力,并且在水藻的生长过程中,氮磷元素的消耗量更大,因此能够促进水体中氮磷元素的迅速降低[18]。此外,由于水藻与蓝藻等争夺营养物质,也导致了蓝藻群落的衰退。此外,网藻的生长也与光照、营养物质和温度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若其生长速度提升,则其养分的吸收容量也会随之提高。此外,温度、光照和氮磷元素浓度等也会导致养分吸收容量的改变。
2.3水生植物除藻
作为水体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大型水生植物能够将光能转换为有机能,并且将氧气释放进入周围环境,因此对生态系统的维护十分重要[19]。在湖泊和水库等水体生态系统中,可以借助大型水生植物对富营养化水体中的藻类进行去除,并且对促进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命活动。在进行水生植物除藻的过程中,应当选择合适的水生植物。能够被用于除藻的水生植物必须同时具备抑制藻类生存和耐污染的能力,即这些水生植物应当能够在富营养化的水体中生存,并且还能够对藻类的生长繁殖进行移植。有学者[20]对国内外的水生植物除藻技术进行了综述,并且将现有已经投入使用的水生植物有挺水植物、浮水植物和沉水植物三种。这些能够用于除藻的水生植物能够分泌一些化感物质(包括长链脂肪酸、简单不饱和内酯、酚酸、酯类、醇类、醚类、酮类、萜烯类、菲类、木质素、苯茶胺等),并且能够对藻类的生长进行抑制,此外还能够争夺水体中的氮磷元素,以促进富营养化程度的降低。另有研究表明[21],人工栽培于富营养化水体中的高等水生植物也能够提升除藻率。此外,有学者将水生动植物和生物载体共同构建了人工浮床,并且发现这一结构能够显著去除水体中的氮磷元素。
然而,细胞凋亡后水生植物的腐烂降低了水体中溶解氧的浓度,容易导致水体变黑、发臭,加速了湖底的淤积和淹没。因此,水生植物的养护处理尤为重要。
我国学者[22]研究了菖蒲、柱头、凤头和睡莲四种水生植物。在静态的情况下收集富营养化的废水,并将其进行水培实验,从而对单一植物与组合植物的生长情况进行研究,并且判断水生植物对氮磷元素、TP和COD的去除效果。实验结果表明,36天后,狐尾藻是单一植物中除藻率最佳的植物,而凤眼莲、菖蒲和睡莲则依次位于其后;在组合植物中,除藻效果最佳的植物组合是狐尾藻+凤眼莲,这一组合能够实现84.7%的氮磷元素去除率和60.95%的TP去除率;而菖蒲+凤眼莲则能够实现85.74%的COD去除率。与单一植物相比,组合植物中的每一种的净增重率都有所下降,这提示我们在组合植物中,不同种类的植物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3结语
目前藻类的季节性爆发问题在河道,湖泊,水库水系都存在,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如何控制藻类爆发依然是目前的热点和难点。生物法控制藻类相比物理法,化学法具有安全、成本低、无二次污染等优点,且能够吸收水中的营养物质,故藻类污染生物去除方法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重点,但大部分的报告是关于单一的处理主要在模拟水体污染物种,和大多数的研究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和探索未来的大规模工业应用。今后的研究将集中在提高处理效率、降低成本、消除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以及研究反应机理等方面。
参考文献:
[1] 潘洁,吕榜军.藻类毒素对健康危害和控制的研究进展[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05 (3) :273~275.
[2] Hart R C. Food web (bio-) manipulation of South African reservoirs-viable eutrophication management prospect or illusory pipe dream A reflective commentary and position paper [J]. Water SA , 2006 , 32(4): 567-575
[3] Zaccara S.Canziani A. Roellaet V, et al. A nort hern Italian shallow lake as a case study for eutrophication control[J. Limnology.2007.8(2):155-160.
[4] Mathes J, Korczynski 1, Miller J, et al. Shallow lakes in Northeast Germany: Trophic situation and restoration programmes[J]. Hydrobiologia, 2003, 506/507/508/509 (1) :797-802.
[5] Chang H Q.Yang X E. Fang Y Y, et al. In-situ nitrogen removal from the eutrophic water by microbial-plant integrated system[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 B,2006,7(7): 521-531,
[6] 王刚,陈杰瑢.水体藻类污染去除方法研究进展.[J]水处理技术.2010.36(9):16-20
[7] 比嘉照夫·人。くらし。生命が変わる, M环境革命M.东京:综合ユニム株式会社, 1994
[8] 李雪梅等.有效微生物群控制富营养化湖泊蓝藻的效应[J].2000.39(1):81-85
[9] 赵以军,石正丽,真核藻类的病毒和病毒类粒子[JJ.中国病毒学,1996,11 (2) :93~102.
[10] 邓建明,陶 勇,李大平,等,溶藻细菌及其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J.应与环境生物报,2009, 15(6) :895~900.
[11] Mayali X, Azam F. Algicidal bacteria in the sea and their impact on algal blooms [J]. Journal of Eukaryotic Microbiology, 2004,51(2) : 139~144.
[12] 刘萍,张吉强固定化溶藻菌除藻效果研究[J]环境工程,2016,28
[13] Watkinson A J,O'Neil J M, Dennison W C. Virus-like particles associated with Lyngby amajuscula (Cyanophyta;Oscillatoriacea bloom decline in Moreton Bay , Australia[J]. Aquat. Microb. Ecol.,2001,25:207-213.
[14] 陈杰,崔鹏,韦方强,等,基于模糊关系理论的冰川泥石流活动性评价方法[J].水土保持研究, 2003, 10(2): 1-4.
[15] 马沛明. 利用着生藻类去除N、P营养物质的研究[D].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2005.
[16] 徐乐中,李大鹏.原位生物膜技术去除水源藻类研究[J]工业用水与废水,2008,39(1):32
[17] 吴为中,王占生.不同生物接触氧化方法对藻类的去除效果比较及其途径分析.[J].环境科学学报.2001.21(3):277-281
[18] 陈汉辉.应用水网藻净化水源水质的初步试验[J]重庆环境科学.1998.20(4):19-21.
[19] Mitsutani A, Takase K, Kitita M, et al. Lysis of Skeletonema costatum by Cytophaga sp. isolated from the coastal waters of the AriakeSea[J]. Nibon Suisan Gakkai-shi, 1992,58(2): 2159-2169.
[20] 洪喻,胡洪营,水生植物化感抑藻作用研究与应用[J].科学通报.2009(3):287-293.
[21] Fang Y Y, Min P P. Ammonium and nitrate uptake by the floating plant Landoltia punctata[J7. Annals of Botany, 2007, 99(2):365-370.
[22]丁海涛等.水生植物对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效果研究[J]佳木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38(1):11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