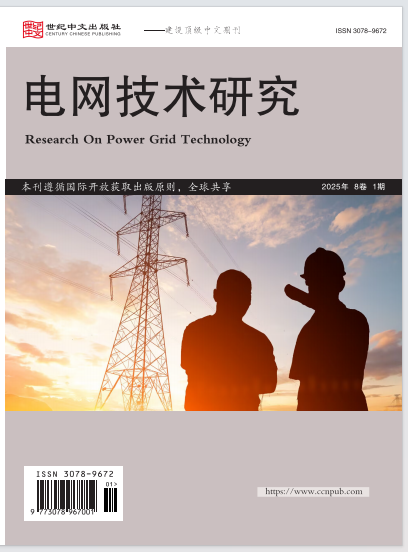一、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风险
(一)电源结构变革带来的供应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电力供应以煤电等高碳电源为主,装机占比始终在50%以上,2020年煤电装机达到10.95亿千瓦,发电量4.63万亿千瓦时,装机占比首次降至50%以下,但发电量占比仍超过60%。
在碳中和目标愿景下,部分省区出台不再新增煤电、减煤限发并加速退出的政策,电力供应转向风、光等低碳电源,但风、光具有明显的随机性、间歇性,光伏夜间出力为零,风电出力低于20%的概率高达50%、出力高于70%的概率不高于10%。据历史资料显示,新疆某地风电低于装机容量20%的低出力最长持续时间超过8天,陕西某地光伏低于装机容量20%的低出力最长持续时间超过4天。间歇性电源供电保障能力弱,而配套的抽水蓄能、储能等灵活性资源又受站址、成本回收机制等制约,发展严重滞后。《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新增抽水蓄能电站1700万千瓦、气电5000万千瓦。截至2020年底,仅完成了目标增长量的47%、72%,较目标值低900万千瓦、1400万千瓦。因此,电力供应或长期处于紧平衡甚至区域性短缺状态。
2020年12月14日、16日、30日以及2021年1月7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创历史新高。特别是2021年1月7日,晚间用电负荷高峰达到11.89亿千瓦,在22亿千瓦电力装机中,2.5亿千瓦光伏出力为零,2.8亿千瓦风电出力仅10%,再加上冬季枯水的影响,3.7亿千瓦水电出力1.7亿千瓦,仅46%,电力供应逼近安全极限。2020年冬季,湖南、江西、浙江、江苏等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限电,居民取暖照明等基本生活保障受到影响。
(二)系统特性变革带来的运行风险
未来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呈现“双高”(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高比例电力电子设备)、“双低”(低系统惯量、低抗干扰性)、“双峰”(早晚高峰、冬夏高峰)等叠加的特征,新的运行特征导致电力系统的频率、电压、功角三大核心特性均发生深刻变化,具体表现为:转动惯量降低导致调频能力下降,无功支撑不足导致电压稳定问题突出,耦合关系复杂导致功角稳定难度加大,电力电子装置易诱发次/超同步振荡。结果导致:一方面,系统的运行风险加剧;另一方面,随着煤电等电网友好型机组的减少,预防、抵御和清除风险使得系统恢复并保持安全稳定运行的措施手段“捉襟见肘”。
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测算,“十四五”期间其经营区域内最大日峰谷差将达到4亿千瓦,最大日峰谷差率(峰谷差与最高负荷的比率)将增至35%,叠加可再生能源的“反调峰”特性,系统的调峰能力将面临较大挑战。
近十年来,我国甘肃、内蒙古、河北等地发生多起风机大规模脱网事故;新疆等地发生宽频带振荡100余次;2015年7月,哈密山北地区风电场产生的次同步谐波引发花园电厂机组轴系次同步扭振保护动作,导致3台66万千瓦机组同时跳机。
其他国家也出现过很多类似的案例,如2019年8月,英国电网线路遭到雷击停运后霍恩风电场脱网、燃气电站停机等连锁故障,损失负荷93.1万千瓦,包括首都伦敦在内多地的100万人受停电影响,社会秩序混乱。
(三)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停电风险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十年一遇”“几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灾害时有发生,传统意义上罕见的极端天气变得更加频繁。2019年,澳大利亚在90天内打破了206项高温记录;2020年,我国浙江省梅雨量破历史记录,7月雷暴天气频发,雷云向地面放电共计20万余次。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天气高度耦合,电力系统面临极端天气负荷需求高涨、化石燃料供应短缺、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降低、发输变电设备故障等风险。
(四)网络外力攻击带来的调控风险
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多点分散接入的特点使得电力系统安全控制难度增大,加之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在电力系统感知与控制中的大规模渗透,如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广域测量系统(WAMS)等,以及源网荷储融合互动需求的增强,导致电力调控系统受到人为外力破坏或通过网络攻击引发大面积停电事故的风险增加。
二、对策建议
(一)坚持各种能源统筹协同发展
以电力安全保障需求为导向,提早研究煤电的去留与定位,推动煤电由“主体电源”向“基础性和调节性电源”转变,统筹电力供应安全与绿色低碳发展;以保障可再生能源消纳为导向,提早研究抽水蓄能、气电、储能等灵活性资源的发展与定位,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与系统消纳能力相适应,统筹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
(二)加快可再生能源角色转变
可再生能源发电正在逐步从“补充电源”变为“主力电源”,作为主力电源则不可再那么“随性”。一方面,加快《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19963-2011)、《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19964-2012)等标准的修订,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从“他助”到“自助”的转变,增强自身的频率、电压等主动支撑能力;另一方面,需完成从“免费”到“付费”的转变。在可再生能源电源自身已经尽力调节的基础上,还需电力系统其它成员提供的调峰、调频、调压等辅助服务,建立合理的市场机制和盈利模式,并按“谁提供、谁获益,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加快并规范辅助服务市场建设。
(三)强化细化电力系统风险管理
对于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建立高预见性、高精度的天气预测系统和极端天气预警系统,按极端天气概率和影响范围,建立差异化的电力保障预案,实现从“临时应对”到“事前预案”的转变,优先保障居民的电力供应,同时应完善网络结构,着力解决电网薄弱环节,加强电网弹性。对于网络攻击风险,应进一步加强安全防护,实现调控系统从“被动防御”到“主动防御”的转变,设置调控设备准入机制,加强漏洞排查,健全事故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提升网络安全事件取证和追踪能力。
(四)加快推动电力系统技术变革
随着可再生能源比例的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将实现从“并网”到“组网”的转变,需超前研究超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机理、仿真分析模型,推动源网荷储和多能互补,避免路径依赖,建立全新的电力系统规划、设计、运行、管理体系。
三、结束语
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愿景,保障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前瞻性地揭示其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并给出有效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我国电力系统的发展现状出发,阐述了未来电力系统的发展目标,基于实际数据与典型案例研究分析了新型电力系统面临的四方面风险:电源结构变革带来的供应风险、系统特性变革带来的运行风险、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停电风险和网络外力攻击带来的调控风险。最后,从能源系统协同发展、可再生能源角色转变、风险管理、技术变革四个角度提出了“六个转变”的对策建议:煤电由“主体电源”向“基础性和调节性电源”转变,可再生能源发展从“他助”到“自助”的转变、从“免费”到“付费”的转变,风险防控从“临时应对”到“事前预案”的转变、从“被动防御”到“主动防御”的转变,技术体系从“并网”到“组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