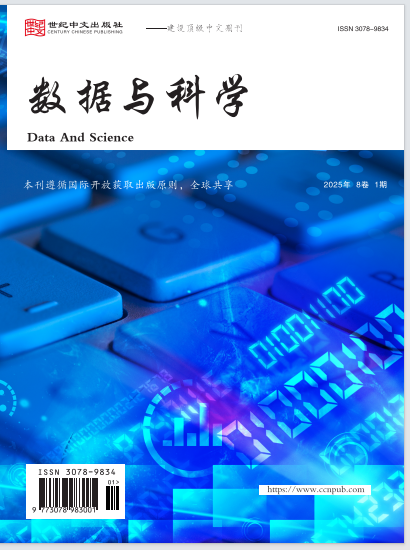伴随着通信方式的更新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网络空间为作案手段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以每年20%的速度迅速增长,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作案成本低,操作简单并且收益很大,这点便吸引了很多犯罪分子加入到该类型犯罪。同时,我国目前并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进行合理规制,这使得很多犯罪行为人不用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低成本、高收益、刑事责任的不对等,都促使更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
根据统计数据,2011年、2012年、2013年全国共发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分别为10万起、17万起、30万起,涉案金额分别达到40多亿、80多亿、100多亿,案件增长比例为70%,77%,涉案金额增长比例为100%,25%。根据公安部的统计,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案件40万起,涉案金额107亿元,比2013年分别增长33%,7%。
近十年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数达到59万起,经济损失222万元,造成的损失达到巅峰。从造成的损失来看,电信网络诈骗相比传统的诈骗案件,危害更大,可以在顷刻间使个人倾家荡产、企业濒临破产。2016年8月19日徐某玉被诈骗9900元上学费用后,于8月21日因伤心过度导致心脏骤停,不幸身亡。2015年12月29日,贵州省都匀市经济开发区建设局杨某某被境外诈骗集团骗走1.17万元,达到单笔被骗数额的最高值。
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增长的迅猛态势相比,侦破率却不足10%,一些地区的侦破率甚至不到2%。究其原因,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多样、隐蔽性强;技术含量高,侦查工作开展困难;多为流动作案和跨境作案,管辖问题与域外司法协助问题难以有效解决;由于技术限制取证困难等,这些问题均给侦查工作带来阻碍,但是其中的取证问题更为关键。
侦查作为刑事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起点环节,证据的收集、提取、保存是主要任务,能够为后续工作展开起到关键作用。根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主要依附于电子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特点,电子数据的问题值得重点研究。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问题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概念
若没有网络,便不会有网络犯罪。犯罪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窗口,它从来不会落后于社会技术条件。网络犯罪区别于传统犯罪的最大特征是“非接触性”,犯罪行为人不用与受害人、涉案财物进行接触,通过电信、网络,即可完成犯罪。这种犯罪形式与诈骗的结合多为电信诈骗犯罪、网络诈骗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2条第2款的规定:“本条例所称电信,是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传送、发射或者接收语音、文字、数据、图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动。”据此,结合《刑法》266条“诈骗罪”的条文,电信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以传送、发射或者接收语音、文字、数据、图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形式,与被害人进行远程接触,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者其他欺骗性手段,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网络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然而在实践中,犯罪行为人往往将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进行诈骗行为,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根据前述定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指,犯罪分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手段或者网络平台向特定的或者不特定的人打电话、发送信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根据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可知,我国并没有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单独构罪,而是将其参照普通的诈骗犯罪要件和量刑幅度进行规制。
(二)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演变
我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于20世纪末在台湾地区兴起,最初采用刮刮乐、六合彩等手段实施诈骗。21世纪初开始蔓延至内陆,其中有两次高峰期。
1.第一次高峰期:2003年-2005年
我国内陆的电信诈骗犯罪兴起于2003年,率先出现在临近台湾地区的福建省。随着台湾地区警方对电信网络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强,诈骗团伙将犯罪地点移至福建厦门一带,并召集福建安溪籍人员进行作案。此时的犯罪主要由台湾地区诈骗组织进行操纵,召集闽南地区无业人员参加。后来福建籍诈骗团伙成员在台湾地区人员的组织下,学会了作案方法,便“自立门户”,由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全国范围内由东南沿海地区向内地蔓延,并逐渐泛滥。
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和内地关系缓和,两岸联手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强度增加,一些诈骗团伙将犯罪地点移至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这为此类案件的侦破工作带来很大的阻力。
2.第二次高峰期:2007年至今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从福建省开始,于2007年蔓延至广州地区,2008年开始在广州地区泛滥。目前,犯罪已经从沿海地区延伸至中部、西部地区,同时,自2008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进入高发态势。2008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省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的损失是6亿元;2009年,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由于电信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高达10多亿元。
(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征
根据公安部刑侦局提供的信息显示,自2008年以来,我国电信网络犯罪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诈骗窝点逐渐向内陆省份和境外转移。二是诈骗犯罪团伙呈现公司化、集团化管理模式。三是作案手段更加隐蔽,境外因素增加。四是诈骗手法逐步升级。”
1.犯罪主体呈现集团化特征,衍生出产业链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为集团式作案模式,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话务组”“办卡组”“转账组”“取款组”等,分散且相互独立,根据各自“业绩”进行分成。
21世纪以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随着通信技术和网络金融业务的更新、发展,也进行了多次“升级改造”,逐渐精细化,由此催生出许多灰黑色产业,这些新产业服务于电信网络诈骗,为其顺利开展提供帮助和技术支持。这些灰黑色产业可以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产业。
(1)以“信息准备”为主的上游产业。上游产业主要是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提供准备工作,如收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网络账号信息、银行账户信息、网络购物信息等,这些信息通过非法出售或其他非法渠道辗转到诈骗团伙手中。如“杜天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作为“陈文辉等7人诈骗”的关联犯罪,前者侵入山东省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网站,非法获取64万余条考生信息,并将其中10万余条提供给后者,涉案金额14100元。
(2)以“建立通讯”为主的中游产业。随着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大,犯罪分子逐渐减少与受害人建立通讯连接的方式。由此,为诈骗犯罪顺利实施提供稳定的通讯线路、网络塔桥服务等连接渠道纷纷涌现,这些产业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不易被追踪,确实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环节。
(3)以“收取资金”为主的下游产业。诈骗行为实施完毕,犯罪分子会急于收取涉案钱款,为了躲避侦查,及时取现,隐蔽且稳定的取现平台成为灰黑色产业滋生的场所。在电信网络诈骗的最后一个环节,有专门的地下钱庄提供资金转移、洗白服务,甚至有专门的背包客通过跨境取现的方式为诈骗团伙提供资金帮助。
2.作案突破时空限制,非接触性强,隐蔽性强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往往盘踞在东南亚国家,如老挝、越南、新加坡、柬埔寨等国家,将用于诈骗的电话、服务器、平台管理等设立在边境地区,而转账取款地点、地下钱庄等散布在境内,这种境内外勾结的作案方式导致一起诈骗案件涉及多个犯罪地点,同时突破时空限制,并利用网络空间的虚拟化特点,掩盖犯罪痕迹和事实真相。同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是典型的非接触性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犯罪行为实施地和犯罪行为发生地之间相互分离,隐蔽性强,这导致犯罪区域的无限性和地域管辖、跨境侦查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
3.犯罪手段多变,技术含量高
为了顺利取得被害人的信任,犯罪手段随着时事热点、社会热点不断变化。如2016年6月至8月陈明慧、范治杰、高学忠等人群发“奔跑吧兄弟”虚假中奖信息;近年抖音短视频平台的“假靳东”“假马云”事件等。诈骗手法已从最开始的“冒充熟人借钱”“冒充法院接收开庭传票”等发展到如今的以电话和互联网相互结合的“杀猪盘式诈骗”“某电视综艺节目中奖”“个人信息泄露需要到营业厅办理业务”“投资理财类诈骗”等,作案手法的多变让被害群众防不胜防,再加上新兴技术的普及,如AI换脸技术、指纹录入等的广泛应用,使得虚假人物形象拥有同真人一样的外貌、声音特征,给人民群众的防范,公安机关的反诈骗宣传、案件侦破工作,带来很大阻力。
伴随高案发率,公安机关的大力宣传,群众警惕性的提高,犯罪手段也在不断变换,以突破群众心理防线,由此犯罪的技术含量也逐渐提高,这便要求犯罪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从一开始的虚构中奖、熟人求救到现在的结合社会热点发送相关信息,这需要犯罪分子能够在掌握大量信息后实现“精准诈骗”。犯罪专业化提高体现在三个方面。
(1)人员专业化。这体现在犯罪行为由经过专业训练的犯罪团伙实施,犯罪分子中很多人掌握了高超的互联网技术,甚至是网络“黑客”,熟练运用各种网络病毒,用来攻击各种类型的网络平台,获取大量所需信息。同时不乏能够熟知受害人心理的“谈话员”,他们有一套精心设计过的话术,可以在短时间内攻破受害人心理防线。
(2)设备专业化。例如“伪基站”、“种植木马”等,这些基本上是电信网络诈骗必不可少的作案工具。
(3)运行专业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出集团化,内部分工逐渐精细,信息收集、话术设计、信息流拆分、资金流转、取现等,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这种连环套似的骗术往往使被害人在诈骗完成后仍深陷其中。
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电子数据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区别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最大特征是“非接触性”,这导致在该类案件侦查中电子数据成为主要证据种类。
我国刑事法领域对电子数据的关注,便是随着计算机犯罪成为新的犯罪形态而出现。2016年9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对“电子数据”进行了明确定义。电子数据所具有的海量性、脆弱性、易丢失、不稳定、技术性等特点,导致若不能及时收集、提取和固定,事后很难再重新收集。
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诸多特征相对应,该类型犯罪中电子数据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分散性
电信网络犯罪的实施需要多台数字化设备的配合,并且电子数据与所依赖的存储介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分离,由此,与犯罪有关的电子数据不仅仅存在于犯罪嫌疑人所使用的服务器中,也会存在于各种可移动性存储介质中,例如U盘、储存卡、移动硬盘、ZIP盘等,甚至可以储存在不同地域的网址中。因此,电子数据具有很明显的分散性,不利于证据收集工作的开展,为证据链的形成带来很大困难。
(二)隐蔽性
传统犯罪可视化明显,证据往往也具有直观性。而网络犯罪的虚拟化特征使得电子数据也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的证据由代码、或者编码组成,以电磁波、光电信号等形式存在于光盘、磁盘中,并且与其他海量数据混杂在一起,再加上犯罪嫌疑人有目的得加密,具有极强的隐蔽性。
(三)易变性强
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远程操作通信设备、计算机等对电子数进行破坏,或者通过病毒植入清除电子数据,另一方面,在取证过程中的不当操作也会造成电子数据的损毁、灭失。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嫌疑人之间,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联系通常为数字化的信息交流,所产生的电子数据能够通过数据加密、数据伪装、信息隐匿等技术被篡改、伪造甚至破坏,加大了电子数据的提取、保存难度。同时,犯罪分子在取得赃款后会迅速进行分流转账、提现、洗钱等程序,使得取证工作涉及的环节多,数量大,难度高。再加上取证时间滞后,侦查人员相关知识的欠缺等,这些原因均导致最佳取证时间延误,很多电子数据被销毁、破坏,造成大量待破解的数据积压,证据体系不完整,取证效率大打折扣。
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电子数据取证的困境
根据前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性,以及该类型案件中电子数据所呈现的特点,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面临着如下问题。
(一)犯罪现场难以勘察
传统犯罪案件具有明确的物理场所,时间、空间明确具体,能够进行现场勘验、调查走访、证据收集、摸底排查等侦查工作,但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物理场所仅限于犯罪分子所在地、数字化设备所在地、取现场所等,并且流动性强。而电信网络诈骗的信息更多的存在于网络中,虚拟空间存有的电子数据更具有侦查价值。
(二)证据难以保全
电子数据往往具有时效性,存在一定的存储期限,要求侦查人员能够及时、准确固定、提取证据,这要求专业的技术和设备支撑。但是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内部专门的技术部门尚且存在技术欠缺、设备不足等问题,更不用说一般的侦查部门。这些导致在打击犯罪时缺少硬件设施,限制了侦查人员对犯罪的研判和打击工作。许多基层的公安机关需要通过层层上报、再经过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关联部门进行取证,复杂繁多的提交和审批程序导致最佳时机的贻误,造成证据难以保全。
(三)电子数据易被篡改、损毁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力度的提升,部分犯罪分子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再利用自身的专业技术,能够第一时间对电子数据进行加密、篡改,甚至会及时删除以至于侦查机关无迹可寻。
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电子数据取证问题的探究
(一)加快专业化队伍建设
基层公安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人员多为普通民警,并不具备适合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技术和能力,复合型人才的欠缺导致案件办理效率低。对此可以进行以下探索。
1.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专业性强的培训场所,培养能够熟识网络通讯技术、工作技能较强的侦查人员,从而整体提升侦查队伍建设。
2.从相关机构聘请专家、教授,作为指挥人员进行技术辅助,以弥补侦查队伍专业性机能欠缺的漏铜。
(二)进行设备优化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电子证据的提取往往需要同网络追踪、无线定位、数据复原等技术相关联,这对公安机关的硬件设施提出了要求。
1.开辟能够迅速获取电子数据的渠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窝点分散在内陆和境外,侦查取证面临程序繁杂、耗时较长的问题。若建立跨区域警务平台合作,进行横向联动,简化材料提交和审批手续,便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网络办案优势,为电子数据的获取提供更加便捷的渠道。
2.加快建立电子数据提取设备。电子数据的提取不同于一般的证据收集程序,要确保数据完整性,尽可能提取原始材料。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电子数据提取设备的建立,确保高科技的取证工具顺利开展。
(三)深化各方合作
1.加强内部警力协作。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及经济、刑事、民事等多个领域,需要公安机关内部多部门进行协作,无论是对资金流、信息流的追踪,还是证据固定,需要公安机关内部协调统一,将经侦、几针、情报等部门进行联动,提升电子数据调查、提取的效率。
2.深化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电子数据的调查取证,必须加强与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合作,对资金流和信息流及时追踪定位,同时建立与第三方平台的联动,充分利用数据资源,通过智能化的侦查措施在大数据中查明、收集、固定电子数据,以期形成证据链条。
结语
由于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不受时空限制,非接触性强,导致被害人不分职业、年龄、性别,分布在各个地区,任何一个网络使用者都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我国手机、互联网用户基数很大,根据相关统计,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1.2%,网购用户规模达到6.39亿,占到整体网民规模的74.8%。非接触性诈骗使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广泛发布经过精心设计的话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加上大数据分析对每个网络用户的生活分析,使得很多网民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的增加,很多犯罪窝点设立在东南亚地区,使用外国的服务器、招募外国人员进行犯罪,即便是国内人员出国进行诈骗,也是办理旅游签证,3个月左右就会更换地点,这对取证问题和罪犯抓捕都造成了困难,不仅仅是国家间的司法主权问题,更重要的是,该类型犯罪为当地财政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有些国家甚至默许基于这些犯罪提供一定的庇护。
电子数据作为电信网络类犯罪的主要证据种类,对于该类型犯罪的侦破具有重要作用,若能够突破该类案件中电子数据取证问题所面临的瓶颈,对电信网络诈骗问题的侦查工作以及后续的诉讼流程将由巨大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 冯鸿波:《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侦查困境及打击对策》,载《森林公安》2020年第3期,第12-13页。
[2] 任鹏飞等:《电信诈骗爆炸性增长》,载2014年10月27日《经济参考报》第5版。
[3] 谷岳飞:《2014年中国“电信诈骗”107亿,代表建议“运营商应担责”》,2022年6月21日访问,
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314/13553181_ 0.shtml.
[4] 徐永胜:《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与警务合作模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5] 秦帅,陈刚:《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侦查研究综述》,载《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36页。
[6] 钱洋:《电信诈骗犯罪侦查难点及对策研究》,载《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4期,第50页。
[7]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2022年6月21日访问,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00671.html.
[8] 秦帅,钟政,漆晨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产业化现象与侦查对策》,载《政法学刊》2022年第3期,第6页。
[9] 强文燕:《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选择》,载《铁道警察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31页。
[10]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2022年6月21日访问,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200671.html.
[11] 《“假靳东”案后续:平台出手打击,律师称受害者或难维权》,2022年6月21日访问,
http://www.chinanews.com/sh/2020/10-16/9314384.html.
[12] 徐小磊,王飞:《电子数据取证与合同备案》,中国金融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13] 孟媛:《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载《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50页。
[14] 王铼,雍晓明:《对利用网络进行诈骗犯罪的侦查取证问题研究》,载《政法学刊》2010年第1期,第79-80页。
[15] 戚沛恩,孔宇庭,毛钱佳成,卢诺然,曾天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电子数据侦查取证问题》,载《法制博览》2022年第7期,第20页。
[16] 于朝辉:《CNNIC发布第4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载《网信军民融合》2019年9月,第30-31页。
[17] 宋光帅:《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对策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0年第12期,第12页。
[18] 卢小倩:《电信网络诈骗的侦查困境及出路》,载《中国新通信》2021年第3期,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