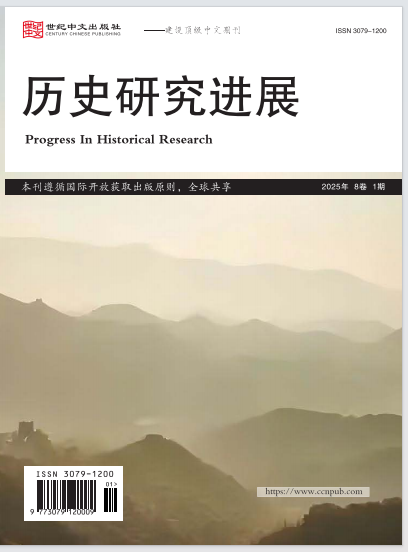一、 引言
彼得·伯克曾说:“文化史学家为什么要涉及语言?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个主题留给语言学家去讨论呢?这里的理由之一是,在任何时候,语言都是一个敏感的指示器,能表达文化的变迁,虽然并不只是个简单的反映。”语言传播是最常见的传播形式之一,语言中的单词、语法也是传播的基础单位。语言的变迁是应对新的社会传播的需求而产生的,同时也会在更大程度上改变整个社会的传播和文化。
回望过去,汉语中的“他、她、它”代词系统也不过短暂的百余年历史。汉语在五四运动之前并没有一个明确区分性别的代词系统,“他”字统称男性、女性甚至是物体和动物,其他东亚文化中语言的代词性别区化的历史也十分短暂,这些新的代词系统都是在各自应对“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仓促出现的。
相较于欧陆语言这种性别区分明显的语言来说,汉语的方块字及其代词自古以来并没有严格的性别区隔或是性别强调。这种文化的冲击和不对称性第一次体现为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翻译时的无所适从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文化优越感,而后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写作者和其他的文化运动家不断努力、创新、争论,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他、她、它”代词系统。女性的“她”字的提出被视为女性地位提高的重要文化标志,从此女性从不可见的“无名氏”变成了可见的“她”。
而在当下却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当时那些因男女、阴阳的明细区隔而相当有文化优越感的西方语言开始朝“性别中立(gender-netrual)”的方向走去了。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字典Merriam Webster把“单数的第三人称代词they”选为了他们的2019年年度词汇,根据这一字典的解释,可以用they指代一个性别不明确的个体,或是表示一个自我认同为“非二元性别身份(non-binary)”或“性别酷儿”的个体。目前“they”除了网络上的火热,越来越多的出版商和严肃写作者开始使用;而早在2012年瑞典就有开始使用性别中立的代词“hen”的正式提议。
如何看待当代西方语言的“性别中立化”现象?当前所提倡的单数形式的“they”是否与中国五四运动前的无性别的“他”是否是同一个东西?汉语或中国文化又将如何对这一新的代词作出反应?笔者试图在性别与传播的视角下探讨以上问题。
二、 语言中的性别与文化内涵
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的,它们各自塑造着对方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其言说者的思维方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并不单纯是社会的产物,它会反过来影响其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鲍文,2007)。人们对于社会的一切观察、认识和解释,都是在特定语言的框架之下进行的,会在无意识中受到语言框架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性别的一切言说自然也都是在特定语言的框架下所进行的,但是许多语言却有着长久而隐秘的性别歧视,比如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以男性来泛指所有人。
从性别角度来对所有语言做一个大致的划分,目前的语言可以分为:(1)“性别化的语言(gendered languages)”,又称“语法性性别语言(grammatical gender languages)”,这类语言的名词都有阴阳性,并且相应的代词、形容词等的形式也要与名词的阴阳性相适应,而相关研究表明使用这类语言的文化性别平等程度明显低于其他文化 ;(2)“自然性别语言(natural gender language)”,这类语言主要是通过代词区分性别,而名词和其他词类则通常不表达性别特性;(3)“无性语言(genderless languages)”,这类语言的语法中对性别区分最为宽松,名词或代词系统完全不区分性别,比如芬兰语中hän作为代词既可以表示男性又可以表示女性(Prewitt-Freilino et al. ,2012)。
除了诸多“性别化的语言”被证实存在性别歧视外,属于“自然性别语言”的英语也一直被女性主义者批评其代词系统存在着性别歧视。英语中的代词he可以指代性别不明确的个体或是泛指任何人,但是有许多的研究表明,大部分的时候读者看到he时会把其指代人物想象成一位男性(Baron & Dennis E, 1986; Kremer & Marion, 1997)。显然这样的语言或文化是带有性别歧视的,女性和其他非二元性别在特定语境下必然处于不可见的边缘地带。因此女性主义者在语言学领域内发起了试图消除英语中的性别霸权、将其改造为一种更为性别中立的语言的一系列运动,而对代词的改造则是重中之重。
对于英语代词的改造最主要有以下尝试:(1)造一个新的代词,(2)使用双重代词“he/she”或“he or she”,(3)用“they”来指代的性别不明确或非二元性别个体而非群体(Baron & Dennis E, 1986)。造新词的办法在英语世界中并不罕见,但是代词是特殊的,并不能像名词或动词一样造出来而不管其流通和接受程度。诸如e/em/eir,hu/hum/hus,ze/hir/hir等新造的“性别中立代词”大多都仅仅流传于LGBTQ群体内部,并没有被主流英语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Pauwels & Anne, 2001)。而使用双重代词“he/she”或“he or she”虽然在语法上没有问题,但是却违背了语言的简洁性,并且he和she的排列顺序也是许多人争论的焦点。
唯一留下的方案也就是目前较为流行的“单数的they (the singular they)”,即用they来指称性别不明确的个体或非二元性别认同的个体(nonbinary individuals)。比起完全新造一个词,they的优势在于其悠久的历史——they在英语中作为一种中性的、非具体的代词的用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Bjorkman & Bronwyn M, 2017),而“单数形式的 they”被判定违反语法的法令则是18世纪才有的,并且从未被完全地废用过(Balhorn & Mark, 2004)。即便如此,“单数形式的they”在今天的含义也不完全是以前的“中性代词”了,更多的是特指非二元性别认同的个体,比如在明确知道对方“生理性别”是“男或女”的情况下,仍然称其为“they” (Strahan & Tania E, 2008)。这种新近的用法具体始于何时还比较难考证,但是近年来使用的趋势逐渐上升。
同样属于“自然性别语言”的瑞典语新造一个中性的代词,于2012年提议使用新的“hen”作为一个中性的代词,与已存的hon(她)和han(他)共同使用。与“单数的they”一样,“hen”一方面可以指代性别未知的个体,另一方面也可以指代诸如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等的非二元性别的个体。研究表明,从2012年到2015年,瑞典公众对于“hen”的态度开始从消极趋向于积极,并且实际的使用也在不断增多,因此造新的代词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Gustafsson Sendén et al.,2015)。
如上文所述,东亚地区的汉语、日语、韩语等属于“无性语言”,所有词类都不对性别做出区分,而区分性别的代词系统也是近代语言改革的新近结果。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西方的接触越发频繁,两种文化知识体系的碰撞和结合在文字的翻译与对应上最早体现出来。
三、 汉语中的人称代词与性别
近代以前,汉语本无区分男女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传统,在与西方语言接触后,这种汉语独特的特点才逐渐成为一种“缺失”而凸显出来。两种文化和语言的不对称首先由第一批来华的传教士所发现,如19世纪的传教士就苦于英文she如何翻译成中文,他们对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性别化翻译做出了初步尝试。今天我们熟知而自然的“他”、“她”之分是五四时期新文化人的创造性贡献——最初刘半农于1920年初在《她字问题》中正式提出使用“她”字,随后在与其他新造字、新意古字的角逐中,“她”字最终得到了最广大社会的认可,“他/她/它”的现代汉语代词体系才最终形成(黄兴涛,2015)。而在“五四”之前,“他”是汉语中运用较为广泛的一个代词,兼称男性、女性以及一切事物,而“她”字最初在古代是作为“姐”的异体字儿存在的:《说文解字》中记载“蜀人谓母曰姐”(张硕,2017)。这种“他”字的泛指性与汉语作为“无性语言”相对应,也成为现代汉语的一种缺陷:“他”字在现代语法中仍然可以泛指,在性别不明、不分性别和男女共存的情况下一般都是用“他”。
在当前“他/她”之分下,也有人在实践层面和学理层面试图进行弥补。在当下网络和一些新闻语境中,比较有性别意识的做法包括用拼音“TA”来避免具体的汉字、采用两者兼顾的“他/她”形式或干脆另辟蹊径用全部“它”字来表示。而钮维敢(2009)则提倡新造一个“ ”(tā )字,在性别不明或不分性别的情况下使用。
虽然目前汉语中没有相应的代词,但我们有必要赶上部分西方语言的“时髦浪潮”,再想一种新的代词吗?同样的问题在“她”字之争中也出现过——刘禾等认为,“她”字的发明是源于中西“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刘禾与宋伟杰,2002);而黄兴涛(2015)教授认为,汉语代词的性别分化不能归结为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而是其自身的现代化需求或现代性诉求正好与所谓的西方性发生了偶然的重合;杨剑利(2015)则认为“现代性”并不能与“西方性”截然分离,“她”字的西方性与现代性是内在而不可分的。
笔者在此赞同黄兴涛教授的观点,我们不能将语言视为静止不变的事物,外部的刺激是可被观察到的最明显的因素,但唯有契合汉语本身发展的改变才会被社会大众和历史文化所接受保留。代词的出现、性别化或是可能新增的“性别中立代词”,都是语言不断自我发展以适应社会和文化的结果。
在古汉语中,人称代词主要的意义是指“三身”:自称、对称、他称。第三人称代词又叫他称,主要有“彼、其、之”等词,它们是指示代词而非第三人称代词(张硕,2017)。在唐代以后“他”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第三人代词,成为汉语中第一个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不分性别的“他”又逐渐分化出阴性代词的“她”,从此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走上了区分性别的道路,“她”字的出现再一次提升了汉语的表达效率和精确度。汉语从本无第三人称代词,到无性别的“他”,再到有性别的“他”与“她”,本身就是语言进化的一种结果。虽然表面来看“她”的出现是为应对西方语言的翻译,颇有西方文化霸权压迫的色彩,但是汉语也没有全盘的西化,而是汉语自身的现代化过程与西方的路径发生了部分重合。
代词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而牵扯到身份认同。“她”字的广泛流传,并不只是在翻译上解决了与she相对应的问题,而是表达了女性在语言言说和书写中的凸显,被当时的新文化人视为男女平等的符号象征,象征着妇女的独立和解放。
欧陆语言第三人称代词隐含性别歧视,因此西方的女性主义者在上世纪就多次发起了“女性主义语言运动”, “单数they”的火爆则是部分因为“非二元性别者”的加入。
非二元性别(Non-binary)可以理解为多种性别身份认同,包括:(1)认为自身性别在男性与女性之间或之外;(2)认为自身性别同时包含男性和女性特质;(3)认为自身没有性别或拒绝一个明确的性别身份(Matsuno, Emmie, and Stephanie,2017)。自我定义为非二元性别者或性别酷儿的人口数量并不少,在地域上来看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都有一定的人口基数,而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拒绝二元性别划分的行为也不是一种“后现代的时髦”。一项荷兰研究发现4.6%的男性和3.2%的女性认为自己的性别身份认同比较模糊,1.1%的男性和0.8%的女性认为自己的性别身份认同与生理性别有冲突(Kuyper, Lisette, and Ciel Wijsen, 2014)。而Van Caenegem等人(2015)的研究数据表明,在比利时约有1.8%的男性和4.1%的女性自我性别认同为非二元性别。在性少数群体中非二元性别的身份认同比例更高——一项英国的调查表明5%的LGBTQ青年认为自己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Chances & METRO Youth, 2014);而一项美国的研究显示13%的跨性别者也“找不到自己所属的性别”(Harrison et al.,2012)。Joel 等人(2014)在2013年在以色列的调查显示在2225个样本中,超过35%的人认为自己或多或少都拥有另外一种性别的体验。
在人口总量上并不少的非二元性别者积极地创新和使用一种“性别中立代词”,除了破除性别歧视,还是一种表达自我身份的途径。相关研究也表明社会中二元化的性别认同与更高的抑郁程度甚至自杀可能性高度相关(Matsuno & Budge, 2017)。而从语言开始,从一个新的代词用法开始,是非二元性别者争取社会认同和自我表达的“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有效平权途径。
或许Facebook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洞见。2014年Facebook在性别选项中的男和女之外添加了一个“定制”选项:用户最多可以从56种其他性别中自定义自己的性别,其中就包括了“非二元性别”、“性别酷儿”和“无性别”等选项。除此之外,用户还必须先要选择一个希望被指称的代词:“他(he)”、“她(she)”和“TA(they)”。其行为逻辑在于,Facebook商业价值恰好与其用户的“真实身份”挂钩,强调其用户的“真实性”——是真人而不是水军,这一“真实”是Facebook吸引投资和广告主的重要手段,也是其创造的“价值”(Bivens & Rena,2017)。基于资本动力的市场行为或许可以成为打破二元性别的助推力,但是也要警惕性别身份过于细化后涉及到的数据隐私被侵犯。
笔者在此讨论代词的性别问题以及汉语代词创新的必要性,认为这并不是语言学的特权和专域,因为其背后是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复杂互动。既然目前汉语的代词系统还存在着种种缺陷,一种新的代词方案就应该被提出用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语言问题,这并不是所谓的文化霸权,而是符合汉语自身发展逻辑的。或许一个新的代词只是挑战男权主义和二元性别的一小步,但是我们绝不能小看语言对于社会文化和个体思维的影响。而这种新代词具体以什么形式出现,是找一个旧字赋予新意,还是新造一个字,才是语言学应该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鲍文. (2007).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解析 (Doctoral dissertation).
[2]黄兴涛. (2015). "她" 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钮维敢. (2009). 现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缺点及补正. 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8(4), 114-116.
[4]刘禾,宋伟杰. (2002). 《跨语际实践—文学, 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社科新视野, (5), 46-46.
[5]杨剑利. (2015). 现代性与 “她” 字的认同——读黄兴涛《“她” 字的文化史》. 近代史研究, 205(1), 139.
[6]张硕. (2017). “他” 与背后的 “她”--汉语单数第三人称代词的流变. 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版), (1),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