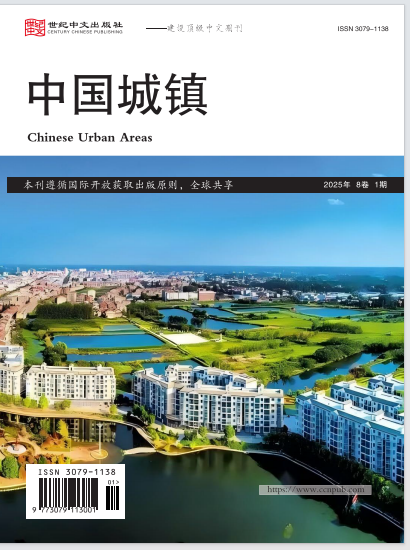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随后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突破菏泽、鲁西崛起的若干意见》,并陆续出台相关具体措施。乡村振兴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全方位振兴,既需要大量的政策和物质资源的支持,同样需要大量具备各方面知识和能力的人才。然而,长期以来,城市由于能够提供更为优越的发展条件和生活条件,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导致农村建设缺乏人才,成为阻碍乡村振兴的瓶颈。由此,乡贤的力量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呼唤乡贤文化回归也成为重振乡村建设的重要思路。“新乡贤”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无疑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新乡贤”内涵和类型的界定
乡贤即传统社会的“乡绅”,也被称为“士绅”、“绅士”等,一直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结构中的中坚力量。乡绅的概念众所纷纭,费孝通先生说,“乡村社会中的绅士,可以从一切社会关系,亲戚、同乡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土皇帝本人。”[1]费正清先生对“士绅”概念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一群家族,狭义上是指通过考试和捐纳取得功名的个人。一般来说,乡绅是指传统乡村社会中有名望,有地位,能以其高尚品质,文化修养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并对乡村社会产生影响的人物。
今天的乡贤与传统社会的乡绅阶层不同,费正清先生认为“新乡贤”是“当前乡村社会中有知识、有品德,生于乡土,回归乡里、奉献乡土,在村民之间口碑好的人。”[2]与传统社会的乡绅阶层相比,新乡贤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所处的历史代新,新乡贤处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下,乡村社会需要城市反哺的新时期;二是其知识储备和理念新,新乡贤多具有现代化的眼光,能为乡村带来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文明理念,或是先进技术,能够将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具有多元化,如退休干部、退休教师、企业家、优秀学子以及各种技能型人才等。他们能利用自身优势对乡村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总之,新乡贤是指在新形势下,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文化修养,综合能力强,能为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的民间贤能之士,他们对维护乡村秩序,延续乡村传统文化,实现乡村经济振兴,维护公共利益,促进乡风文明,实现乡村的良好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二、“新乡贤”培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培育更多的“新乡贤”可以更快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而“新乡贤”的培育根植于良好的文化环境,需要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对新乡贤的积极的、正面的、统一的认识,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文化建设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当下的新乡贤文化建设,需要解决新乡贤服务于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诸如要转变社会观念、政府行为、个体行动等。
(一)要解决传统乡贤认识观念与新乡贤文化建设之间存在矛盾。中国的传统乡贤文化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其传统认识观念对人们的思维影响根深蒂固。乡贤是从乡村走出的成功人士,他们有令乡人敬仰其学识水平、道德水准和成就,但他们可能长期远离故土,和故土的关系疏远甚至断裂,如家乡的土地、房屋、户籍关系等早已没有了,他们回归乡村,如无特别情况,对于乡村中的事务多抱以“观望”态度。从村民视角看,也多认为回村乡贤是“客体”。这就造成了村民与乡贤之间关系的疏离,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改善,势必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如期实现。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3] 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的实现难度大,不仅仅是资源问题,也是人才的问题,需要新乡贤发挥模范引领作用,不仅是为乡村事务建言献策,提供各种资源,而且新乡贤可以身体力行,回乡自主创业,在发展乡村经济中起到带头作用等等。而传统的乡贤观念认识狭隘,已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当下新型乡贤文化建设的需求。
(二)要解决传统乡贤服务方式与新乡贤文化服务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乡贤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服务乡村:一是通过自身的道德情操和成就为村民树立精神典范,影响村民的道德水准,激励村民努力上进,从精神引领上为乡村服务;二是通过提建议、做参谋的方式为乡村建设服务。这两种途径曾对乡村发展产生过一定作用,但并没有充分发挥乡贤的主观能动性。新乡贤的服务渠道单一,缺乏必要的服务平台,服务渠道不畅通,方式僵化,都影响着新乡贤们充分发挥自身信息、资源、技能方面的优势,不能达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调动利用一切力量的要求。
(三)要解决传统乡贤激励机制与新乡贤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乡贤回归故里多是告老还乡,并不愿意过多承担乡村具体事务。即便是他们愿意对乡村建设做贡献,也仅仅是出于乡情,碍于情面。导致传统乡贤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不足的原因是乡贤激励机制的缺失。人本主义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激励机制,人们都有获得他人尊重和社会认可的心理需要。所以乡贤激励机制的缺失是不利于吸引更多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的,更不能有效激励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作用。这与让新乡贤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带动农村精神文明和经济建设、引领乡村建设等目标相距甚远,不符合现代乡贤文化发展的要求。[4]
三、“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角色和路径
新乡贤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多元化,这既是传统的延续发展,又是现代社会转型变迁的结果。传承与转型,影响着新乡贤的特质类型和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方式。
根据新乡贤的类型特质,新乡贤主要分为“精英型新乡贤”和“平民型新乡贤”,并根据其生活居住空间和主要收入来源是否在乡村,分为“在场的新乡贤”和“不在场的新乡贤”。一般来说,精英型新乡贤的收入来源和生活居住空间都在城市,属于“不在场新乡贤”; “平民型新乡贤”的生产生活主要在乡村社会之中,属于“在场的新乡贤”。[5]不同类型的新乡贤,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角色和路径不同。精英型新乡贤主要致力于乡村产业兴旺、村民致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而平民型新乡贤则主要在乡村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有较大成效。
(一)精英型新乡贤的参与路径
精英型新乡贤有党政干部、企业家、专家学者、从本地走出去的明星等,他们虽然出生于乡土,但却功成名就在城市,收入来源、居住场所、社会关系和人情往来都已经远离乡土社会,因此他们很难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振兴中来,无法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但由于他们成长于乡土,对故乡也有情感,一部分人也有意愿和能力支持故乡实现振兴。他们有较多的资源,尤其在市场信息、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外部关系和金钱资材等方面,他们能预估未来发展趋势,有较宽的发展视野,能为乡村振兴带来较多的资源和发展机遇。一些眷恋乡土的成功人士,愿意捐钱捐物,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 一些企业发展和自身利益涉及到农业、农村的企业家、商人等,也有更强的动机和意愿投入到乡村振兴中来,并参与到农业发展、乡镇企业、乡村旅游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方面。具体途径包括以建言献策、乡村顾问、投资产业、开拓农村市场、招商引资、项目承包、农村基建、捐钱捐物、村务监督等方式,从而发挥他们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就业、农民富裕以及民俗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菏泽有很多从村庄走出去的成功人士,他们有较强回报家乡的意愿,经常为家乡的发展提供物力和财力支持,通过捐资修祠堂、庙宇、道路、水利的方式,回馈家乡。他们这类虽没有精力亲身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资材”回报家乡,尤其表现在对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的贡献上[6]。除了捐钱捐物,一些商人和企业家,也以发展产业、承包工程和项目的形式介入到乡村社会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处在鲁西南,经济欠发达的菏泽人口外流严重,富人群体难以真正扎根在乡村社会之中。不乏一部分资本和商人,借乡村振兴和新乡贤发展的之机,下乡圈地赚钱,与民夺利。一些产业振兴的项目,也可能演变为一些资本和商人攫取利益的机会,特别是当前的项目承包、农村基建方面,很容易成为他们返乡谋利的机会[7]。一些“旅游村”和“富人典型”,已经成为不少富商群体谋取自身利益的途径[8]。因此,尽管我们倡导和允许各类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但在村务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角色和路径要有一定的限度,并不主张富商资本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因此,精英型乡贤应当主要是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出钱出力,并不实际介入到乡村治理中来为好。
(二)平民型新乡贤的参与路径
平民型新乡贤成长于乡土,并没有脱离农村,他们的时间、精力、收入和社会关系都在乡村中,所以能亲自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中来,他们依赖自身的知识、能力、道德、声望和公心,顺理成章地成为乡村公共事务的带头人和群众中的领头人。
平民型新乡贤与村民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往来和利益关系,能够与村民建立真正的互惠关系和信任关系,也能够在村庄公共事务上平等协商,并可以用自己的声望、人情、面子等,组织、动员村民一起行动,共同解决村庄事务。因此,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的先进典型,才是“新乡贤”的主体[9],他们连同普通村民是真正的乡村振兴主体[10]。
更关键的在于,平民型新乡贤通过动员群众,能群策群力解决乡村振兴中的难题。他们以自己的时间、精力、技术和文化,真正投入到农业生产、文化礼俗、公共品供给、乡村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中来。他们以个人或组织的形式,如成立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村落理事会、监督委员会等,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并能发挥引领村民的作用。他们在村民中的影响力和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让他们可以很好地协助村两委助力乡村振兴,成为连接村民和村干部中的一环。除了成立民间组织以外,一些积极分子和个别较有威望的人,也会作为小组长、村委干部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
但是平民型新乡贤也有其弱势,就是个人的经济基础和资源较为稀缺,并没有足够的信息和资源来带动乡村产业的发展,也没有较多的社会资本和权威资源来实现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治理,很多时候,往往需要借助外部资源和力量来达成自身的目标。
菏泽经济欠发达,存在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双薄弱困境,长期以来难以激发外部资源的投入。但目前这种现状大大改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源向农村注入,这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乡村振兴资源不足的局面。这为平民型新乡贤发挥作用,提供了有效的物质保障,解决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也激发了村民建设乡村的热情。
处于鲁西南的菏泽当下实现乡村振兴较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国家资源与乡村社会的有效对接? 如何发挥新乡贤在联结村庄社会和国家资源的中介作用?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吸取先行地区的一些好的做法,例如在经济和文化资源都较为薄弱的农村地区,政府部门可以组织长期居住在村庄的退休老干部、身边好人、道德权威等组成了村落理事会,当地政府不仅要赋权赋名帮助他们树立威望,还要输入资源帮助他们开展乡村建设和村庄公共活动。村落理事会不仅在乡村治理、村庄文化建设上发挥了较多作用,还在村庄公共品建设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有效地解决了项目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11]这间接方便了农民的生产和当地产业的发展,村庄逐渐被激活,越来越多的村外力量被引入进来,形成了内外联动、群众参与较多的局面。[12]
村落理事会的成员大都属于平民型新乡贤,他们可能是一些小型家庭农场主、农机和农技人员,也可能是运输司机、小商小贩群体,或者是一些退休老人群体。他们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但能够在村庄中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负担并不重。并且,由于他们长期生产、生活在农村中,有较多的时间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一些积极分子、有“公心”的群体也愿意为村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部分人逐渐成为村庄社会的“身边好人”“道德权威”等。[13]
综上所述,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的今天,对新乡贤内涵和类型进行了重新界定,解决好新乡贤培育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新乡贤”,探讨符合他们自身特征的参与乡村振兴的角色和路径,无疑对乡村振兴、突破菏泽战略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费孝通.皇权与绅权[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133.
[2](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33.
[3]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传递六大新信号.新华网.2017-12-30.
[4]邓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困境与途径[J].学术论坛,2018(3):172.
[5]高万芹.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和参与路径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2018,36(3):132.
[6]罗兴佐.第三种力量[J].浙江学刊,2002( 1) : 24-25.
[7]李祖佩.项目进村与乡村治理重构——一项基于村庄本位的考察[J]. 中国农村观察,2013( 4) : 33-45.
[8]王海娟,贺雪峰.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J].学习与探索,2015 ( 2) : 72-84.
[9]本刊综合.创新发展乡贤文化[J].人民文摘,2014( 10) : 24.
[10]贺雪峰.乡村振兴战略: 农村基本保障不能市场化[N].第一财经评论,2018-01-03.
[11]龙斧,高万芹.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民主治理机制[J].湖北社会科学,2016( 11) : 33-40.
[12]高万芹,龙斧.村民自治与公共品供给的权利义务均衡机制——以 Z 县 G 乡 L 村为个案[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16(5): 38-45.
[13]杨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探寻执政党政权在农村社会的阶层基础[J].战略与管理,2010(5/6): 35-46.
作者简介;冯帆(1972-),男,汉族,山东菏泽人,硕士,菏泽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史和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