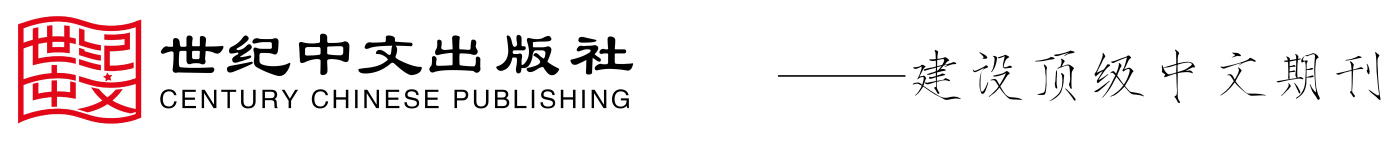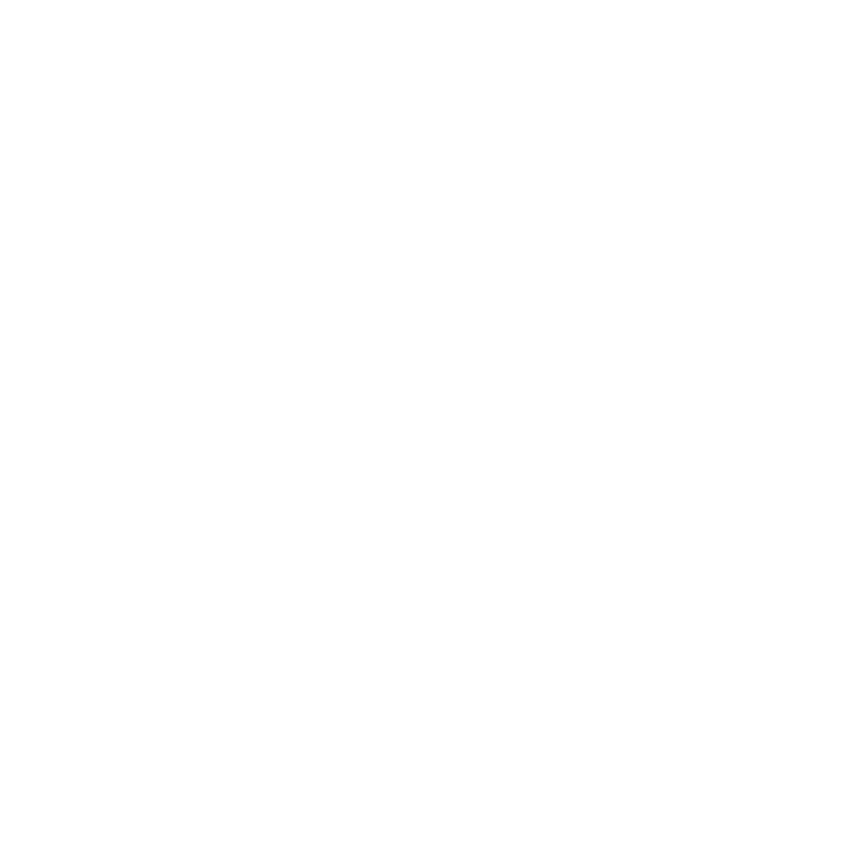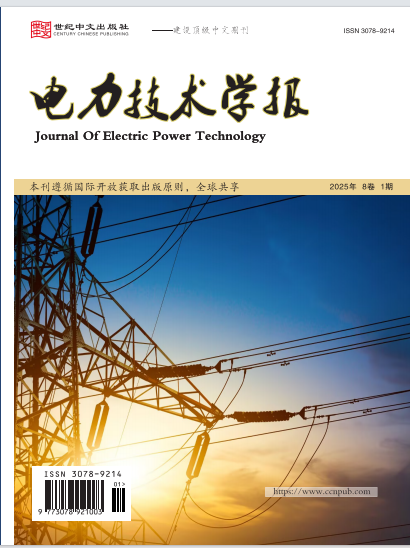2019年底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感染导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爆发不同程度的NCP疫情,并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1]。医务人员作为本次疫情防控的一线参与者,不仅要面临高强度的疫情防控工作,还要担心可能被感染的风险,容易引起各种身心疾病。本研究旨在了解基层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为下一步针对性的身心健康教育及心理危机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0年2月-3月期间重庆市南岸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疫情防控期间在岗的全体医护人员为调查对象,自愿参与问卷调查。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基本情况问卷 通过查阅文献并咨询相关专家后,拟定抗击NCP疫情期间可能影响医护人员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婚姻状况、学历、家人是否被隔离、所属部门、岗位、自评岗位风险、是否会因工作担心家人感染、是否有信心做好防控工作。
1.2.1.2 量表介绍 在GAD-7中,受试者被问及关于焦虑症的7个问题在过去14天被困扰的频率。回答选项依次为“没有”、“偶尔”、“经常”和“总是”,对应分值为0、1、2和3,总分范围从0到21,0-4分代表正常,5-9分代表轻度焦虑,10-14分代表中度,15-21分代表重度。在PHQ-9中,受试者被问及关于抑郁症的9个问题在过去14天被困扰的频率。回答选项依次为“没有”、“偶尔”、“经常”和“总是”,对应分值为0、1、2和3,总分范围从0到27,0-4分代表正常,5-9分代表轻度抑郁,10-14分代表中度,15-19分代表中重度,20-27分代表极重度。SSS-8是躯体症状量表-15的8项简短版本,受试者被问及关于躯体症状的8个问题在过去7天被困扰的频率。回答选项依次为“没有”、“偶尔”、“有时(没有超过一半的时间)”、“经常(超过一半的时间)”和“总是”,对应分值为0、1、2、3、4,总分范围从0到32,0-3分代表正常,4-7分代表轻度躯体障碍,8-11分代表中度,12-15分代表重度,16-32分代表极重度。
1.2.2 调查方法 首先联络各科室负责人,取得各科室医护人员的配合,统一采用“网络问卷”的调查方式收集资料,问卷指导语说明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填写方法等。调查对象在5-10min独立填写并提交问卷,每个选项均设置为必答选项。共收到有效问卷198份。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符合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M和四分位间距(Q1,Q3)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ANOVA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两组间相关性采用Spearman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的部门主要分为门诊(包括发热门诊、急诊、隔离区)、内科、外科和辅助科室(包括检验科、放射科、超声科、药剂科)共198名医护人员。其中女性136人(68.7%),男性62人(31.3%);年龄:<30岁69人(34.8%),30-39岁81人(40.9%),40-49岁34人(17.2%),50-59岁10人(5.1%),>60岁4人(2.0%);独生子女105人(53.0%),非独生子女93人(47.0%);未婚46人(23.2%),已婚146人(73.8%),离异或丧偶6人(3.0%);本科以下132人(66.7%),本科及以上66人(33.3%);医生83人(41.9%),护士115人(58.1%);岗位风险为自评感染2019-nCoV风险高低程度,其中低危86人(43.4%)、中危57人(28.8%)、高危55人(27.8%)。
2.2防疫期间医护人员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现状 抗击NCP疫情期间医护人员GAD-7得分无焦虑139人(70.2%),焦虑59人(其中轻度焦虑45人(22.7%),中度13人(6.6%),重度1人(0.5%));PGQ-9得分无抑郁141人(71.2%),抑郁57人(其中轻度45人(22.7%),中度10人(5.1%),重度1人(0.5%),极重度1人(0.5%));SSS-8得分无躯体症状障碍120人(60.6%),躯体症状障碍78人(其中轻度59人(29.8%),中度14人(7.1%),重度3人(1.5%),极重度2人(1%))。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共病49人(24.7%)。
2.3防疫期间医护人员GAD-7、PHQ-9、SSS-8评分与各因素组间比较 结果显示:女性、护士、本科以下学历、独生子女、岗位风险越高的医务人员GAD-7、PHQ-9及SSS-8评分更高(P<0.05);门诊较内科、外科GAD-7、SSS-8评分更高(P<0.05),较内科PHQ-9评分更高(P<0.05),辅助科室较内科GAD-7评分更高(P<0.05);未婚组较已婚组GAD-7、PHQ-9、SSS-8评分均更高(P<0.05),离异或丧偶组较已婚组仅SSS-8评分更高(P<0.05);担心家人感染的医务人员PHQ-9评分更高(P<0.05),年龄<30岁组较30~39岁组SSS-8评分更高(P<0.05),而是否有家人被隔离及是否有信心做好防控工作各组间无论在GAD-7、SSS-8还是PHQ-9评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2.4 医护人员GAD-7、PHQ-9、SSS-8得分与各因素Spearman相关性分析
GAD-7得分与性别、岗位、岗位风险呈正相关性,相关系数(ρ)分别为0.356、0.392、0.492(P<0.05),与学历、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呈负相关,相关系数(ρ)分别为-0.329、-0.156、-0.158(P<0.05);
PHQ-9得分与性别、岗位、岗位风险呈正相关性,相关系数(ρ)分别为0.330、0.392、0.385(P<0.05),与学历、是否担心家人被感人、是否独生子女呈负相关,相关系数(ρ)分别为-0.311、-0.142、-0.195(P<0.05);
SSS-8得分与性别、岗位、岗位风险呈正相关性,相关系数(ρ)分别为0.360、0.379、0.394(P<0.05),与学历、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呈负相关性,相关系数(ρ)分别为-0.276、-0.182、-0.206(P<0.05)。
3讨论
3.1 医护人员焦虑、抑郁和躯体症状障碍较普遍 目前关于医务人员焦虑、抑郁患病率的研究较多,NCP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更是得到空前关注。但很少联合医务人员躯体症状障碍的研究。国外学者通过网络结构分析[2]显示焦虑、抑郁和躯体症状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联系,研究这些症状的同时发生,能更全面了解被调查者的心理健康状况。Gong Y等[3]在我国医生中进行的多中心调查结果显示25.67%有焦虑症状,28.13%有抑郁症状,略低于本研究结果。究其原因可能受本次传染病疫情的影响较大,疾病传播速度快,医护人员取消春节假期参与到疫情防控中,且基层医院医护人员缺乏相关经验,面临社区排查、发热病筛查、咽拭子标本采集等防控任务,工作压力巨大。其次,不同工作岗位防护级别不等,长期处于密闭或高级别防护状态下容易出现高应激状态,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或躯体症状障碍。
3.2 医护人员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的相关因素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女性、护士、学历低、岗位风险高、是独生子女均为医护人员焦虑、抑郁和躯体症状障碍的危险因素。邹志礼等[4]对四川省人民医院在职员工的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医务人员的躯体化、忧郁、焦虑、强迫、敌意等各项指标评分均高于男性医务人员。然而庞伟等[5]对急诊科医护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医生的抑郁风险更高,可能与调查人群差异、地域差异有关。在我国传统家庭思想影响下,多数女性不仅需要操持家务、照顾子女及老人,现阶段还要参与到疫情防控中,更易出现身心疲惫导致各种心理问题。
晏丽等[6]研究纳入唐山市450名医生与650名护士对比结果显示护士抑郁、活动迟滞维度等方面得分均较医生低,但在医护人员学历方面比较无统计学差异,与本研究有所差异,可能是入选人群及评分量表不同等原因导致。婚姻状况与焦虑、抑郁和躯体症状障碍有相关性,苑杰等[7]对唐山市4所医院医务人员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未婚及离婚丧偶是医生发生焦虑或抑郁的危险因素。本研究也显示未婚组较已婚组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离异或丧偶组较已婚组更容易出现躯体症状障碍,因此,已婚是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保护因素。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岗位风险越高、是独生子女的医护人员产生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障碍的风险更大。作为独生子女的医务人员,尤其从事发热门诊、隔离病区等感染风险高的医护人员可能存在“因密切接触而被感染”的心理恐惧[8],以及感染后对无人照看的父母和子女更多的担心。由于近距离接触疑似或确诊NCP患者,医护人员需要三级防护,穿隔离衣、戴N95口罩、护目镜以及双层手套的使用增加医护人员工作难度,门诊医护人员是医院的窗口,接触病人多且复杂等原因。
我们对各量表之间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提示焦虑和抑郁、抑郁和躯体症状障碍、躯体症状障碍与焦虑均存在正相关性。进一步说明躯体症状与焦虑、抑郁能更全面的评估心理健康状况。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到位,相信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对减轻医护人员的身心障碍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Lai CC, Shih TP, Ko WC, et al.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and coronavirus disease-2019 (COVID-19): The epidemic and the challenges [published online ahead of print, 2020 Feb 17]. Int J Antimicrob Agents, 2020,105924.
[2] Bekhuis E, Schoevers RA, van Borkulo CD,et al.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nd somatic symptomatology. Psychol Med,2016,46(14):2989–2998.
[3] Gong Y, Han T, Chen W, et al. Preval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related risk factors among physicians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PLoS One, 2014,9(7):e103242.
[4] 邹志礼,黄雨兰,汪瑾宇,等.综合医院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实用医院临床杂志,2015,12(6):78-81.
[5] 庞伟,何丽琴,陈智伟.急诊科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与患者满意度的相关性调查[J].海南医学,2014,25(8):1227-1229.
[6] 晏丽,郭鑫,庞静娟,等.唐山市医护人员抑郁症状临床异质性研究[J].职业与健康,2019,35(17):2358-2361.
[7] 苑杰,尚翠华,张蒙,等.2016年唐山市4所医院医护人员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及与心理弹性的关系[J].职业与健康,2017,33(21):2918-2922.
[8] 柴洁.减缓SARS病房护士心理压力的对策[J].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03,35(S1):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