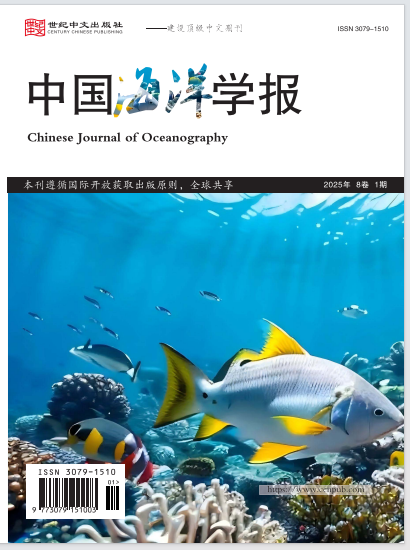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的绊脚石,并且深深影响东亚地区的稳定。自1968年发现钓鱼岛周围海域丰富的石油资源之后,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就正式浮出水面,而其中牵涉的不只是钓鱼岛主权的归属问题,还包括双方的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以及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出现的专属经济区划分问题。争端在中日建交后采取了被“搁置争议”的解决方式,但在冷战结束后,由于各方利益的变动,日本增加了对钓鱼岛动作,有关钓鱼岛主权的矛盾也在21世纪成了中日之间的重大问题之一。中日双方有各自的立场,矛盾难以在现有国际法下调和,需要一套新的制度体系解决争端,在此背景下,习总书记于2019年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或许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重大龃龉。
1. 中日海洋争端矛盾点
中日双方立场对立强烈,矛盾难以调和。中国和日本之间有关东海的矛盾是中国同周边国家海洋争端问题的缩影,都是涉及到大陆架划界、专属经济区划界、岛屿在划界中的地位问题。
在大陆架划界上,中国主张东海大陆架是中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冲绳海槽是具有显著隔断特点的重要地理单元,是中国东海大陆架延伸的终止,[1]因此应该按照自然延伸原则划界。专属经济区则根据1998年6月2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二百海里”。[2]
日本方面则认为中日属于同一大陆架,海沟在两国间的大陆边的延伸上只是偶然的凹陷,双方应该按照等距离中间线原则划定中日的东海界限。[3]专属经济区同样为二百海里,因此和中国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重叠区域。而在钓鱼岛的划界效力上,中国学者主张无效力,日本学者则一部分认为有效力,日本政府虽未明确表态,但基于其对冲之鸟礁和南鸟岛礁的主张,从逻辑上看是认为钓鱼岛可以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4]
此外,对于钓鱼岛的相关条约解释,双方同样各执己见,而根据现行法律,几乎不可能确定哪方会占上风。[5]
2. 国际法解决争端的局限
由于通过国际法解决领土争端的局限性,我国不倾向于采取此种方式解决领土争端。现在中国对钓鱼岛争端的态度是不会诉诸国际法院,[6]而启动法律程序需要主权国家的同意,国际法并不能强制各国接受任何国家或国际机构的管辖,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是无法通过国际法院来解决的。我国不采取法律方式解决的原因之一是考虑到国际法院的局限性。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中存在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于领土争端的复杂性和国际法院自身的问题。[7]
领土争端问题本身及其复杂,往往是需要从历史上进行溯源,涉及条约、主权的继承等等。如钓鱼岛问题首先就需要从历史资料中去证明其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并非无主地。此外也涉及到各类条约具体内容,条约的解释,如《马关条约》《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旧金山和约》等等,以及美日在“冲绳归还”中私相授受钓鱼岛,就进而还需要考察钓鱼岛从历史上、各类条约上与琉球的关系。并且领土主权涉及一国的核心问题,因而非常敏感,也牵涉各个国家的民族情感。
除了领土争端自身的复杂性外,国际法院的管辖与裁判范围具有局限性,从而造成国际法院审理范围无法覆盖完全,即使判决完成后,依然存在争议部分。[8]且国际法院作为一个人为设立的组织,由法官进行审判,也就必然会有时代的局限从而影响判决的真正公允。即使不考虑时代局限性,仲裁程序具有明显对抗色彩,[9]无法给出更利于当事方合作的裁决方案。由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并非是强制性,因此在解决有关领土争端的案件上,有了判决后争端也并不一定能迎刃而解。现实情况是一些争端依然要回归政治的、外交的方式去谈判,甚至是武力交火。
现行的国际法制度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问题的解决,[10]“一刀切”的国际法律制度做法难以适应东亚地区的政治地理环境。国际法鼓励“展示主权”惩罚“默示”,容易造成争端双方民族主义高涨、矛盾加大,政治行动被民族情绪裹挟,难以达成双方的和解。此外,现有法律原则的可塑性造成双方都能够通过援引国际法证明主张合理性,也就造成争端以现有国际法标准难以判断孰是孰非。
3.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平解决中日海洋争端
新的时代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平解决中日海洋争端问题。鉴于国际法院难以在现有的国际法基础上进行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争端解决,国际社会和中日之间需要一套新的理念来指导相关实践的进行。习总书记在2019年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弥补了国际社会上的这一空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包括 “海洋安全共同体”“海洋利益共同体”“海洋生态共同体”以及 “海洋和平与和谐共同体”,[11]倡导“共商、共建、共享”。[12]
中日双方存在运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解决争端的基础。中日钓鱼岛争端因自身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难以真正解决争端,“管控分歧”更为现实,在此情况下“和平搁置争端”是一种实际的选择。[13]实际上,有关中日钓鱼岛问题,早在中日建交时,中国就提出了“搁置争议”,之后发展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种构想也的确有效地推动了中日的建交,但是以现在的局势来看,这个构想并没有被完全付诸,一是日本之后并不承认当时和中国就此构想达成了一致,二是中日双方也未能在争议海域“共同开发”。不过,虽然21世纪以来有关钓鱼岛问题爆发过几次比较大的冲突,但是现在钓鱼岛局势基本上稳定,在危机后,双方也进一步协商。中日双方于2012年1月建立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以来,截止去年已召开十三轮磋商,磋商内容主要是涉海问题及海洋交流合作。2018 年6月,双方也正式启动运行了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从现实双方的合作来看虽然日方对外不承认在建交时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且认为钓鱼岛属于日本是不存在争议的,但是日方实际上在目前也是比较倾向于同中国处理好钓鱼岛的争端问题,不愿意因钓鱼岛争端损害两国的现有关系。此外,中日之间就东海各类争端在21世纪以来也进行过多次谈判,取得一定的进展。日方的态度也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推动建立了事实上的环境基础。在国际上,也不乏多种合作开发的例子,如1989年澳大利亚与印尼之间有关东帝汶海的协定、1990年马来西亚同泰国之间的协定等。[14]在有关争端解决上,“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平等协商,是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一脉相承。
3.1 构建信任机制
中日双方的协商与合作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础之上,为促进中日海洋的争端解决,构建双方的信任是必不可少的一环。[15]而信任建立在合作的深入上,促成东亚国家间海上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为经济的需求。[16]为促进信任的架构,中日需要在“海洋命运共同体”下开展双方的海洋贸易合作。海洋贸易合作涉及多个方面,如具体的降低关税、商品订购、航道运输等。在现在具体实践上,最引人瞩目的就包括RCEP生效。RCEP是中日之间的首个自贸协定,随着两国之间零关税产品覆盖率大幅提高以及区域累计原产地规则的实行,将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贸易规模,拓展更广阔的服务贸易市场,且中日两国跨境投资门槛将进一步降低,第三方市场合作也将迎来更多机遇。去年,中国也申请加入CPTPP,无论是否成功,中日之间经贸合作上的整体的趋势是不断向好的。此外,双方在保障航道安全、共同应对海洋污染等非传统海洋安全等合作上都有非常大的空间。总体而言,经济方面的合作应作为两国之间的“压舱石”来考虑,[17]并由此推动下一步的进行。
3.2进行东海开发合作
在经济合作成功的基础之上需要进一步深入中日东海争端的探讨合作。现在中日双方的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是很好的范例,在此基础上双方应继续推进防务交流活动,增强中日安全互信。加强并巩固“海空联络机制”,积极进行海上对话,探讨东海划界以及共同开发东海油气资源的合理方案。[18]并且应根据国际法,加强中日之间的外交协调,努力减少分歧,以达成双方满意的划界方案作为核心目标开展争端解决合作。中日至今未能达成“共同开发”的一个原因在于双方对这个词的定义有分歧,对开发的区域、合作的方式有不同的理解,若要使双方能够搁置争端实现共赢,还是需要通过对话达成各自的妥协,比如争端岛屿钓鱼岛不具有划界效力、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统一边界等,使主权问题和边界问题分离。[19]
3.3强自身海洋力量建设
在推动合作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中国自身海洋力量的建设。一是加强主权活动合法性及正当性。如我国在2013年在东海划定了钓鱼岛海域和空域的防空识别区,并在近年不断加强钓鱼岛巡航,且出台了《海警法》,使中国海警机构的海上维权执法活动更有法可依并增加了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二是结合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高我国海洋经济实力。三是深度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海洋治理。中国于1973年加入国际海事组织,1996年5月批准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近年也积极参与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协定的谈判,[20]总体上从资源、经济、环境、权益四条路线推动海洋强国建设。[21]
4. 结语
中日之间的海洋争端的问题在于双方主张冲突下,难以达成对争议区域的利益共享,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则正好在于扩大合作的共同利益和范围,持续共享海洋空间和资源利益,即达成利益共享。现在中日之间关系较为稳定,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中日间合作环境更为融洽,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在加强自身海洋力量建设的基础上,同日本构建更为紧密的海洋贸易合作,以助推现行的中日海洋安全合作。在合作中建立信任机制,推动中日之间“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最终实现对东海的“共同开发”。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中国政府提交东海部分海域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EB/0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14/c_114033302.htm,2012-12-14.
[2]. 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法[EB/0L]. http://www.npc.gov.cn/zgrdw/npc/bmzz/aomen/2007-12/07/content_1382501.htm,2007-12-7.
[3]. 吴辉.从国际法论中日钓鱼岛争端及其解决前景[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10(1):80.
[4]. 严峻.东海争端中的台湾因素研究[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96-97.
[5]. Harry R. A Solution Acceptable to All? A Legal Analysis of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 Dispute[J].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ume 46, Issue 3 Fall 2013.
[6]. 界面新闻.中方是否考虑过将钓鱼岛问题诉诸国际法院?中国驻日本大使官方回复[EB/0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0852900994958814&wfr=spider&for=pc,2020-10-18.
[7]. 罗欢欣.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局限性[J].法治论丛,2010,25(1):120.
[8]. Keith Suter. The Successes and Limi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J].Medicine, Conflict and Survival , October-December 2004, Vol. 20, No. 4 (October-December 2004):344-354.
[9]. 余敏友、雷筱璐.南海诸岛争端国际仲裁的可能性——国际法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64(1):6.
[10]. Ramos-Mrosovsky C. International Law's Unhelpful Role in the Senkaku Islands, U. Pa. J. Int'l L.29 (2007): 903.
[11]. 姚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涵: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J].当代法学,2019,(5):138.
[12]. 翟崑.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需知行合一[J].太平洋学报,2020,(1):97-102.
[13]. 黄瑶.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和平搁置争端[J].中国社会科学,2019,(2):113-114.
[14]. 栗林忠男. 排他的経済水域・大陸棚の境界画定に関する国際法理-東シナ海における日中間の対立をめぐって[J].東洋英和大学院紀要, 2006:11.
[15]. 宫笠俐、叶笑晗.“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亚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构建[J].东北亚论坛,2021,(5): 105-106.
[16]. Nguyen Thi Lan Anh. Prospects of Maritime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THE FUTURE OF THE SEAS IN EAST ASIA:: FORGING A COMMON MARITIME FUTURE FOR ASEAN AND JAPAN[J].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Jan. 1, 2015:45-51.
[17]. Euan Graham. Divining the Fluid Element: From Cooperation to Conflict in Japan-China Maritime Relations[J]. Security Challenges , 2015, Vol. 11, No. 1:49-72.
[18]. 高兰.海洋命运共同体与中日海洋合作——基于海洋地缘政治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10下:99.
[19]. Mark J. Valencia. The East China Sea Dispute: Context, Claims, Issue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Asian Perspective[J]. Special Issue on "Reconcil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2007, Vol. 31, No. 1:127-167.
[20]. 段克、余静.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20-21.
Liza Tobin. Beijing’s Strategy to Build China into a Maritime Great Power[J].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 Vol. 71, No. 2 (Spring 2018): 1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