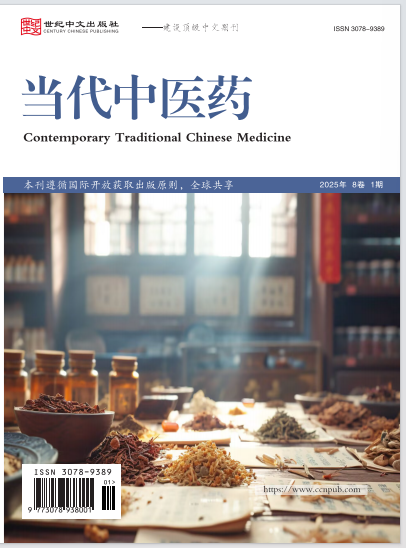口臭,又称口气,是人体呼吸运动时从口腔中散发出来的有臭味的气体,身边之人可嗅及,本人能够嗅及或不能嗅及,口臭对人们的社交活动及心理状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1]。WHO已将口臭作为一种疾病来进行报道。有调查显示,中国口臭发病率为27.5%[2],国外北美口臭发病率为50%[3],男性多于女性,并且口臭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
口臭在中医学典籍中又名“口气臭”、“臭息”、“腥臭”、“口气秽恶”等[4]。口臭病因比较复杂,目前尚无统一辨证分型,根据查阅书籍及文献研究[5-6],常见的中医证型有脾胃积热、寒热错杂、肺经积热、饮食积滞,脾肾阳虚,虚阳上浮等等,笔者临床上运用中医辨证的方法来治疗口臭,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
一、病因病机
历代典籍对口臭的病因病机有不同的记载。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说:“口臭由于五脏六腑不调,气上胸膈......而生于热,冲发于口,故令臭也”。指出了口臭由于脏腑积热引起。宋代赵佶《圣济总录》说:“口者脾之候,心脾感热蕴积于胃,......随气上出熏发于口,故令殠也。”认为口臭由于心脾之热积于胃所致。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劳郁则口臭,凝滞则生疮口。则是从劳倦、气血瘀滞的角度来论治口臭。明代李梴《医学入门》说:“脾热则口甘或臭,口臭者胃热也。”认为口臭是脾热和胃热引起。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说:“口臭虽有胃火,也有非火之异。”提出口臭虽然多由胃火所致,但也可有食滞、脾虚引起,治疗不能一概用清热法。清代吴谦《医宗金鉴》中说:“口出气臭,则为胃热。”认为口臭是胃热引起。又提到“凡口臭,有胃火,亦有胃弱不能化食。”又指出与脾胃虚弱有关系。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说:“脾热则口臭,虚火郁热蕴于胸胃之间则口臭,心劳味厚之人亦口臭,肺为火烁亦口臭。”指出了口臭有脾热、肺热、心劳、虚火、郁热之分。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说:“口气臭是瘀血所致”,提出用血府逐瘀汤治疗。
综上所述,口臭病因有脾热、胃火、肺热、食滞、情志、劳倦、血瘀、脾虚、肾虚等,其中脾胃功能最为关键,脾胃主运化、收纳,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脾胃是气机升降枢纽,外邪内因导致脾胃升清和降浊的功能失调,从口腔到肛门的浊气上泛是关键所在,浊阴不降,胃气逆上,则见口中秽臭。另外是肾阴不足,虚火上炎也可导致口臭。
二、西医病因
口臭可分为口源性口臭、非口源性口臭、精神性口臭[7],具体如下:
口源性:牙周疾病,假牙,口腔干燥症,口腔溃疡,黑毛舌,坏死性口炎,口腔幽门螺杆菌,遗传性感觉和自主性神经病Ⅳ型,饮食因素等。
非口源性:消化道疾病,呼吸道疾病,吸烟,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血液病,糖尿病,维生素缺乏,中毒等。
精神性:又称假性口臭,这类患者别人没有闻到口臭,但是患者自己感觉有口臭,而且临床检查没有明显异常。
这么多病因中,临床上相对比较多见的是牙周疾病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8]。
三、临床验案
1、寒热错杂型
黄某,男,46岁,教师,2019年12月4日初诊。患者诉口臭1年余,近期加重,稍感上腹部胀闷不舒,无腹痛,纳差,伴心烦口苦口干,大便溏薄伴粘液,小便短,睡眠不安,舌红,苔白腻稍带黄,脉滑。诊断:口臭,证型为寒热错杂,治则为辛开苦降。给予半夏泻心汤化裁: 姜半夏10g,黄连3g,干姜9g,远志10g,黄芩9g,党参10g,红枣15g,砂仁6g,炙甘草6g,共七剂,每日一剂,水煎至200mL,分2次温服。
二诊,服用七剂后,患者诉口臭较前明显减轻,腹胀缓解减轻,胃纳仍然欠佳,大便溏薄,小便调,夜寐较前稍安。舌淡红,苔薄白腻稍带黄,脉滑。效不更方,在前方基础上加木香、白术、神曲,加强理气健脾开胃,。药用:姜半夏10g,黄芩9g,黄连6g,党参10g,干姜9g,红枣15g,砂仁6g,远志10g,炙甘草6g,木香6g,白术12g,神曲12g,共七剂,每日一剂,水煎至200mL,分2次温服。
三诊: 再次服用七剂后,患者诉口臭基本消失,上腹部胀闷消失,胃纳好转,大便基本成型,一日一次,小便调,夜寐好转。舌淡红,苔薄白,脉滑。前方稍加调整,药用:姜半夏10g,黄芩9g,干姜 9g,远志12g,黄连3g,党参10g,红枣15g,砂仁6g,炙甘草6g,木香6g,白术12g、苍术10g,神曲12g,共七剂,每日一剂,水煎至200mL,分2次温服。
此后随访诸症基本缓解,嘱其清淡饮食,不能过食肥甘厚腻,不食冷饮,停药半年病情未再复发。
按:半夏泻心汤出自医圣张仲景《伤寒论》:“伤寒五六日......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及《金匮要略》:“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半夏泻心汤证的方证,传统解释有[9]:“寒热之气互结”,“少阴表邪误下,寒反入里,阻君火之热化,结成无形气痞”,“胃脘虚寒,肠中浮热”,“表邪乘虚陷里,与胸中素有之湿浊交相互结”等等。黄煌教授总结其方证为“上呕,中痞,下利,内烦”。现代众医家加减化裁治疗痞证、腹泻、焦虑症、口腔溃疡、皮肤病、宿醉的临床经验屡见不鲜,而治疗口臭则少见,本例患者究其病因病机,亦有脾胃之气受损,导致中焦升降失调,邪气入里郁而化热,熏蒸胃内腐食臭败之气,由胃循于口则见口臭,此为异病同治。
2、脾胃积热
张某,男,53岁,2019年10月9日初诊。患者诉口臭3年余,加重1月余,伴口腔溃疡,牙龈出血,无腹痛腹胀,纳可,心烦,口渴,大便秘结,小便短黄,夜眠欠安,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诊断:口臭,辨证脾胃积热,给予清积除热。给予清胃散化裁: 生地黄20g,天花粉15g,川牛膝10g,当归10g,牡丹皮10g,黄连3g,升麻10g,生大黄6g。共七剂,每日一剂,水煎至200mL,分2次温服。
二诊,服用七剂后,患者诉口臭明显减轻,口腔溃疡愈合,牙龈出血止,胃纳稍有下降,大便通畅,小便调,夜寐好转,口渴、心烦缓解。舌淡红,苔薄黄腻,脉滑。效不更方,因患者大便已畅,胃纳稍差,在前方基础上减少大黄用量,加谷芽、神曲。药用:生地黄20g,天花粉15g,川牛膝10g,当归10g,牡丹皮10g,黄连3g,升麻10g,生大黄3g,炒谷芽15g,神曲12g,共七剂,每日一剂,水煎至200mL,分2次温服。
三诊: 再次服用七剂后,患者诉口臭基本消失,其余诸症均缓解,胃纳亦恢复正常,大便黄软,一日一行。前方稍加调整,药用:生地黄15g,升麻10g,当归10g,牡丹皮10g,天花粉15g,黄连3g,炒谷芽15g,神曲12g,共七剂,每日一剂,水煎至200mL,分2次温服。
此后随访诸症基本缓解,嘱其清淡饮食,不能过食辛辣厚味之品,停药随访一年病情未再复发。
按:脾胃积热型的患者多喜欢辛辣、肥腻食物,导致湿热郁于脾胃而化热,热火灼烧浊气向上,而导致口臭。宋代《太平圣惠方》说: “口臭是由五脏六腑不调,导致体内雍滞之气冲发于口”。清胃散源于李东垣《脾胃论》,功能凉血清胃,方中以黄连为君,清除胃腑之热,升麻为臣,宣达郁遏之伏火,生地黄滋阴凉血,牡丹皮清热凉血,亦为臣药。当归养血活血,为佐药。升麻引诸药上行,有使药之功。清胃散中诸药合用,清泄胃火,养阴生津,对于脾胃积热型的口臭,有着非常好的疗效。后世医家扩大其引用范围[10],其的治疗范围较前有拓宽,如治疗可治疗因胃火上攻之牙痛等疾病。孙克等[11]对利用小鼠进行的实验研究,得出了清胃散能治疗胃热证型的小鼠的胃黏膜、舌黏膜及舌苔变化。张万岱[12]通过研究发现清胃散对幽门螺旋杆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3、肺经积热
刘某,女性,34岁,2020年7月15日初诊,既往有鼻窦炎史,患者诉反复口臭2年余,伴鼻塞,咽部不适,偶有咳嗽,痰少色黄,口渴喜饮,胃纳一般,大便干,小便短,夜眠欠安,舌红苔黄腻,脉滑。证属肺经积热,治宜清肺泻火,给以泻白散化裁:桑白皮15g,地骨皮15g,黄芩9g,桔梗10g,杏仁9g,苍耳子10g,白芷9g,连翘10g,甘草6g。共七剂,每日一剂,水煎至200mL,分2次温服。
二诊,服用七剂后,患者诉口臭较前减轻,鼻塞缓解,大便通畅,小便调,夜寐好转,诉咽部仍有不适感,咳嗽较前减轻,偶有咳嗽几声,痰少不易咳出,舌质淡红,苔薄黄,脉滑。前方基础上加用薄荷、浙贝,药用:桑白皮15g,地骨皮15g,薄荷10g,黄芩9g,桔梗10g,浙贝母10g,苍耳子10g,杏仁9g,连翘10g,白芷9g,甘草6g。继续服用七剂,每日一剂,水煎至200mL,分2次温服。
三诊: 再次服用七剂后,患者诉口臭已经消失,其余诸症均缓解,效不更方,给予前方减去连翘,黄芩,以防寒凉伤胃,药用:桑白皮15g,地骨皮15g,桔梗10g,薄荷10g,杏仁9g,苍耳子10g,白芷9g,连翘10g,甘草6g。共七剂,每日一剂,水煎至200mL,分2次温服。
此后随访嘱其清淡饮食,不吃辛辣刺激之品,停药随访半年病情未再复发。
按:本例口臭乃肺经积热所致,由外邪内伏于肺,则有咳嗽、咽部不适等症状,又肺开窍于鼻,鼻部亦易受邪,所以常有鼻部症状,用清肺泻火之泻白散而收效。泻白散是经典名方,它出自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方中桑白皮甘寒性降,清肺泻热,地骨皮甘寒,清肺降其中伏火,加用连翘增强清肺热,咳嗽加用桔梗、杏仁,鼻渊加用苍耳子、薄荷、白芷,甘草养胃和中、调和诸药。全方配伍,清中带润,泻中带补,清泻肺中之伏火以消郁热。
四、心得体会
口臭在多数中医内科学教材中未作为一个单独的疾病,多列在其他疾病的一个症状,在部分实用中医内科学中有简单附录搜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医文献对口臭的研究也较少,中药治疗口臭的进展不多,现代研究表明,中药起效的原理有:中药富含多种抗菌消炎药物,可抑菌杀菌,中药某些成分可阻碍致臭物质的产生,部分中药含有天然的芬芳剂,掩盖口臭产生的气味[13]。并且中药所含的天然成分毒副作用较小,其治疗效果优于西医。但是口臭病因比较复杂,病机多变,临床当审证求因,利用中医辨证思维,对证下药,这样才能提高中医药对口臭的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王凤磊,李静,茹淑瑛,等.口臭的中西医诊治新进展[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9,17(7):119-121.
[2]LiuXN,ShinadaK,YaegakiK,Oralmalodor-relatedparametersintheChinesegeneralpopulation.JClinPeriodonto,l 2006,33:31-36.
[3]Delanghe G,Ghyselen J,Bollen C,et al.An inventory of patients’re sponse to treatment at a multidisciplinary breath odor clinic[J].Quintessence.
Int,1999,30(5):307-310.
[4]陈小洪,冯培民.中医药治疗口臭的现状[J].光明中医,2014,29(1):205-207.
[5]王晓琳,郭太品.基于文献计量学的中医治疗口臭病因、中医证型、证素分布规律研究[J].中医临床研究,2017,9(32):25.
[6]王永炎,严世芸.实用中医内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341.
[7]朱博文,马维杰,刘佩玉等.口臭的病因及治疗[J].黑龙江医学,2003,27(6):430-431.
[8]王凤磊,李静,茹淑瑛等.口臭的中西医诊治新进展[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9,17(7):120.
[9]黄煌.经方方证[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2:269.
[10]徐重明,汪自源.古方清胃散方义探讨[J].江苏中医药,2005,26(2):38-39,
[11]孙克,张晓丹,杨铭,等.清胃散清胃热作用的实验研究[J].中成药,2008,30(6):812-815.
[12]张万岱.中医药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研究现状和展望[C].第六届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及消化疾病诊治临床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华医学会,2011.
[13]张迪,刘长虹,章锦才,等.西吡氯铵含片对口源性口臭患者口腔内致臭菌的影响[J].南方医科大学学报,2014,34(9)1386-1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