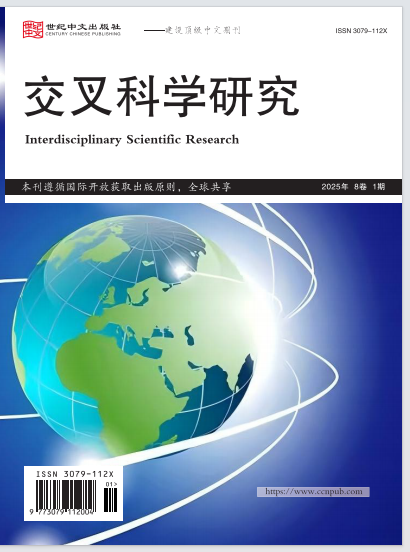2018年“范冰冰”偷逃税案、2021年“薇娅”“雪梨”偷逃税案及2022年邓伦偷逃税案等系列案件的频发,涉案金额动辄上亿甚至数十亿,让人们对高收入、高净值人群的关注度越来越多。然而,如何对高净值人群更好实施税收征收与管理,也引起无数人的思考。
一、高净值人群的界定通常情况下,高收入、高净值人群称为“双高”人群,但两者的范围是有所不同的。高收入是相对于低收入而言的,高收入人群是以收入为标准进行划分的,高收入人群的判断标准随着社会中个人或家庭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而高净值人群是以个人或家庭资产净值的多少位标准进行划分的。一般来说,高收入人群不一定是高净值人群,高收入代表财富的流入量,高净值代表财富的存量,较高的财富流入量并不代表有较高的存量,财富存量的多少还取决于财富的流出量,即个人或者家庭的开支。但高净值人群往往拥有较多的收入来源,称为高收入者,也就是说,以高净值作为衡量一个家庭或者个人的存量财富的多少较为客观。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对高净值人群的划分标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文本参考胡润研究院及贝恩咨询和招商银行联合发布的《201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对高净值人群的界定,将个人或家庭拥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界定为高净值人群,这里的可投资资产主要是包括:现金、存款、股票(指上市公司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债券、基金、保险、银行理财产品、境外投资和其他境内投资(包括信托、基金专户、券商资管、私募股权基金、私募证券基金、黄金和互联网金融产品等)、投资性房地产、非上市公司股权等;而不包括自用住房、自用车辆等非投资性质的耐用消费品。
二、高净值人群税收征管与监管存在的问题
随着金税四期的逐步推进,我国正向“以数治税”的时代迈进,银行、税务实现了信息共享。中低收入者和工薪阶层逃税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税收服务和监管的中心也逐步转移到了高收入、高净值群体。由于人才、制度、技术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我国针对高净值人群的税收服务和监管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我国对高净值人群的界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高净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界定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和消费水平等诸多因素去。当然,国家税务总局可以不设定具体的标准,可以有各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总和因素考虑,但各省在确定具体的高净值数标准时,确定的依据是什么,测试标准的方法是否科学等等,都要经过进一步的论证。
(二)对高净值人群税源的监管存在一定的难度
由于高净值人群的收入结构呈现多元化,收入区域呈现跨区域及跨境等特点,给我国税收税源控制方面增加了难度。虽然金税四期的到来,实现了银行税务的信息同享,除金融机构外,外汇管理、国土资源、车辆管理等部门也未和税务机关数据形成信息共享平台,加之财产登记和国际税收信息交换机制尚不健全,致使税务机关难以获取高净值人群的境内外所有收入信息。
(三)缺乏个人所得税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
许多发达国家,都对本国的高净值人群建立了风险评估机制。如美国,对高净值人群专门进行审计,重点审查高净值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同时“穿透”到高净值人群背后所涉及到的企业、机构等,全面了解和监督高净值人群的纳税情况。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对针对高净值人群进行的审计,更没有关联到高净值背后的企业及机构。
三、加强高净值人群税收服务与监管
(一)明确高净值人群的划分标准
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把划分高净值人群的标题的权限下放到各个省。但国家税务总局应该就确定高净值人群参考的基本指标、运用的方法等,做一个系统的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等可以在这个基本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他因素,在基本标准测算的基础上,有一定程度的上浮幅度。
(二)建立纳税人识别号并进行分类管理
首先,建立完备的高净值人群纳税人识别号。类似于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给每一个自然人纳税人也建立一个纳税人识别号,并将改纳税人识别号与纳税人的银行卡、不动产登记、股票证券、机动车登记等信息关联起来,并专门建立高净值人群档案,并对该人群实施专项审计。
其次,对高进行人群进行分类管理。在设计纳税人识别号时,可以考虑将不同职业体现在纳税人识别号中,比如,在纳税人识别号的某两位位数代表职业,假设01代表高薪员工、02代表文体明星、03代表自由职业者、04代表企业家、05代表独立合伙人等。这样就可以分解纳税人识别号,来判断高净值人员的职业,从而根据收入来源特点进行有针对性性的分类管理。比如,企业的高管或者企业的投资者,应充分挖掘其背后企业数据信息,实施“穿透”分析,重点对股权转让、股权激励、大额资产转让、跨境交易、股息红利等特定事项进行监管;而对文体明星行业的高净值人群,重点监管是否存在“阴阳合同”等方式隐瞒收入、拆分收入、收入费用化、交易“地下”化等事项。
(三)建立高净值人群纳税人诚信档案和奖惩体系
首先,在现有的征信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全国高净值纳税信用数据库。现有的征信体系只包括在银行办理过贷款业务的自然人个人的信息,一般也在申请贷款或者申请信用卡的时候影响纳税人。建议在现有征信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高净值人群的征信影响范围,使其在社会形象、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产生激励和惩戒作用。
其次,尝试实施高净值自然人诚信积分体系。税务部门要制定高净值人群诚信计分的实施细则,根据实施细则,采用科学的方法累计计算高净值人群的累计积分。同时,税务机关需要和其他部分实施联动,将诚信计分纳入到银行信贷、公职招聘、评奖评优、职位晋升、行政审批等考核方面,对于公众人物,则可以尝试给与公开表扬等方式,给予积分高的诚信纳税人以实质性的激励。相反的,对有重大失信的高净值人员采取联合惩戒的措施。对于失信纳税人可以根据情节轻重采取行政性惩戒措施,对纳税人失信情节较轻的,可以采取如依法依规限制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招标投标政府外包项目、享受税收优惠、股票发行等;如果情节比较严重,可以考虑采取限制获得银行授信、限制购买机票、高铁动车票以及在网络媒体上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惩戒措施。
参考文献:
[1] 苑新丽 霍彦蓉. 我国高净值人群反避税问题研究 [J]. 国际税收,2020(5):
59-64.
[2] 吕雪玲.高净值人群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及对策研究 —基于CRS规则[D].广东财经大学, 2019.
[3] 乐娟.高净值人群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及对策研究 —基于CRS规则[D].安徽财经大学, 2020.
作者简介:
许爽(1986.6-),性别:女,民族:汉,籍贯: 河南省驻马店市学历: 硕士研究生,职称:讲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