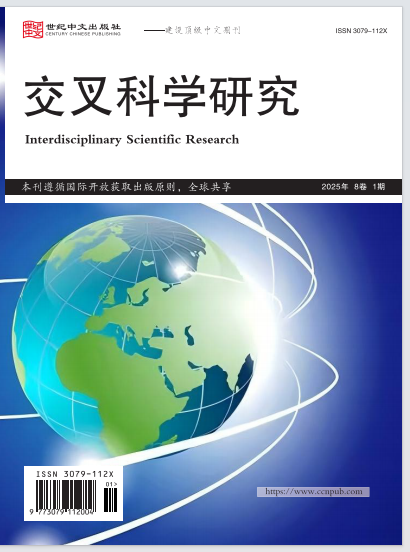一、新乡贤组织的概念演进
乡贤制度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被孕育发展,是十分具有中国特色和历史深度的文化表现。“乡贤”从其字面含义而言,就是对乡村社会发展具有突出贡献的贤能人士。乡贤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代,发展到西汉时期,对巴蜀地区影响最深远的乡贤当属文翁,以致于班固在其《汉书》中称赞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四川地区至今还有以文翁命名的学校,可见一个好的乡贤对于一个地区的历史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乡贤发展到唐代时期,地方志开始对其进行记录,“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是对乡贤进一步的肯定。乡贤发展到现在,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内涵,第十三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提出了“新乡贤”这一概念,由此新乡贤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对于新乡贤的具体含义目前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界定,只是相关学者进行的学理探讨。要明晰新乡贤和中国传统社会中乡贤制度的区别,首先就是要明确其“新”在何处。
首先,新乡贤应当具备新思想和新理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冲淡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伦理和宗族为本位的思想,而乡贤具有的“乡绅”色彩也随之淡化。但是目前我国很多农村地区还是存在较强的宗族观念,其影响力并没有传统中国社会那么大,但是乡村社会所依赖的地缘、血缘和亲缘等因素而形成的宗族伦理思维还是存在的,因此这也给新乡贤这一模式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让新乡贤能够在农村地区发挥新的作用。因此新乡贤所具有的思维不仅应当具有传统乡贤的内容,更应该将新时代中法治、德治、自治的思想融入到新乡贤思想体系中,也应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伦理道德与传统乡贤观念相结合。这样一来,不仅继承了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还为传统道德观念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更是为新乡贤进一步促进农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其次,新乡贤应当具备新的情怀。新乡贤不仅只是依靠血缘宗族等因素来为乡村发展助力,也可以是因为个人情怀和责任担当而进行的奉献,这也是不同于传统的一点,不仅是为了家乡而付出,也能依据“心系农村发展”的情怀而成为一个地区的新乡贤。
二、新乡贤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现状问题
(一)新乡贤作用定位不清
对于乡村地区人才引进不足的问题,新乡贤可以作为有效的补充,但新乡贤对于乡村地区发展中具体定位却是模糊的。在实践中有些乡村地区只是将注意力放在了新乡贤的捐款或捐物之上,而并未对新乡贤所作的贡献予以有效的肯定,这并不利于日后新乡贤的“可持续贡献”。并且,新乡贤对于农村地区的作用并非只是经济援助这么简单,而是作为人才力量、文化传播力量来增强乡村地区发展动力,新乡贤能够在乡村中所起到作用不容小觑,但定位模糊这一问题长期来看只会减少新乡贤的投入积极性。
(二)吸引新乡贤动力不足
传统中国社会中,乡贤所依靠的是血缘地缘等宗族伦理的纽带,将自身与乡村发展进行绑定,从而来带动乡村发展。但是新乡贤单独依靠以前的纽带已经不再牢靠了,因为现代社会中走出乡村地区,这样的观念会进一步被冲淡,原有的纽带也会逐渐瓦解,这就需要乡村地区与新乡贤建立起新的纽带,重新建立起彼此有机的互动。换言之,乡村地区需要有除亲缘等之外的因素来吸引新乡贤荣归故里。但是乡村现有的文化吸引力与新乡贤的文化基因难以产生共鸣,让新乡贤对于乡村发展无法具有认同感和共同的使命感,缺乏情怀的号召力。并且现有的乡村地区也并未采取积极措施与新乡贤加强联系,也很少开展邀请新乡贤返乡参观新乡村发展的活动,这让新乡贤无法切身感觉到乡村发展的前景和潜力,也不利于增强吸引新乡贤的回归动力。
(三)保障新乡贤权益机制不健全
当新乡贤归乡参与到乡村振兴工作中时,乡村并未建立起完善的新乡贤保障机制,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乡贤的工作积极性,并且对于新乡贤本身的公信力而言也具有影响。新乡贤回归故乡促进乡村发展的同时,并不能只是依靠情怀来开展后续工作,而是需要乡村层面予以更多的权益保护,完善整体保障机制,让新乡贤最大程度的发挥人才优势。而对于新乡贤权益保障不仅关乎物质保障,还缺乏精神层面的权益保障。如若乡村居民无法做到对于新乡贤返乡行为的尊重和鼓励,对于新乡贤先进思想的认同和接受,无疑也会阻碍新乡贤权益保障的完善。此外,保障新乡贤完善了解乡村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在实践中,对于乡村政策了解不到位、不全面、难操作等因素都在进一步的阻碍新乡贤的反向进程。
三、充分发挥新乡贤组织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功能
(一)协同村民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独有的具有创新性的政治制度,但目前乡村地区的自治也面临着很多困境,制度运行以及制度创新方面不足,乡村居民对于自治也并无具体性的理解,无法很好的维护自治权利。村民自治内容广泛,涉及民主选举、村民事务公开、村务监督等,这些自治制度的运行都可以很大程度促进乡村民主的发展,而新乡贤的加入则是对村民提升自治水平的加速器。新乡贤对于村民民主选举的参与,可以让村民进一步认识到选举权对于公民而言的重要性,可以很大程度的提升村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更好的维护村民的政治权利,提升村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新乡贤加入到村民事务当中去,不仅可以提升村民自治机构的决策科学性,还可以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机构民主号召力,对于村民自治事务具有创新性提升,并且还可以加强对村民自治机构的监督,村务公开事务更具透明性和信服力。
(二)协同村民提升法治建设水平
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加强乡村法治建设水平,而目前的乡村法治建设处于“虚化”状态,乡村法治氛围并不浓厚,村民法治观念较为缺乏。而新乡贤的加入必定要提升乡村的法治氛围、提升乡村整体法治建设水平。首先,新乡贤的加入可以提升乡村普法水平,为原有几乎停滞的普法工作加入润滑油,让其重新运作起来,通过拓宽普法渠道、增加普法活动、提升法律服务等活动多方位的对乡村居民进行普法活动,不断提升村民的法律意识,起到认识法律,运用法律的领头羊作用。
(三)协同村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新乡贤作为从乡村走出去又走回来的人才,村民对其具有更高的道德期待,很大程度上新乡贤就是村民心中的道德标杆,从而以此为道德标准,更加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和对子女的道德教育。这对于乡村整体的乡风提升具有很大的优势,乡风文化建设这一系统的提升最核心的就是乡民道德的整体提升,而新乡贤协同村民整体提升乡村道德水平无疑是弘扬民风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从而进一步提升道德在乡村治理中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曾凡木.制度供给与集体行动: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分析[J].求实,2022(02):84-96+112.
[2]宋才发.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释放及法治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1(12):24-30.
[3]宋才发.《乡村振兴促进法》为共同富裕提供法治保障[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6(06):1-11.
[4]李岁科.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困境与优化路径[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1,13(04):26-34+153.
[5]李华胤.治理型中坚农民:乡村治理有效的内生性主体及作用机制——基于赣南F村的调查[J].理论与改革,2021(04):116-128.
[6]付翠莲,张慧.“动员—自发”逻辑转换下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J].行政论坛,2021,28(01):53-58.
作者简介:
刘鑫岳(1996- ),男,汉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