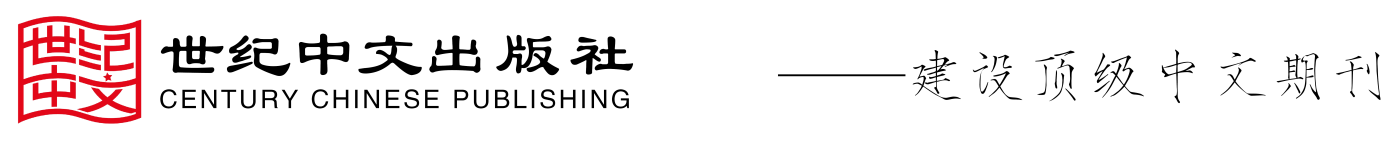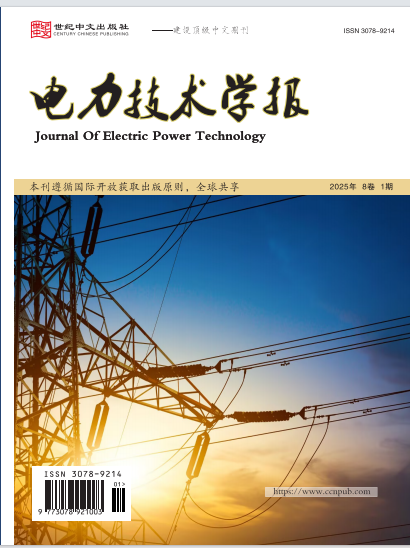文人画在中国绘画艺术中具有绝对的代表性,但在当下“文人画”似乎成为了中国美术史上的概念性名词,并被“消极”、“出世”、“孤傲”等词语覆盖,其深刻的精神性价值却被忽略。随着当今画坛对中国画创作的制作性、和视觉效果的新奇性之追求愈加强烈,对于文人画的讨论和呼声逐渐弱化。这一现象对中国美术发展,和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思想的传承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故在当下重新审视传统绘画中的文人画艺术,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艺术独有的观念,自唐代文人画艺术主张萌芽时期,至后来经历千年不休的争论和演变,历史上一系列的大家都在其中,进行着思想上的思辨和艺术上的变法,这包括:王维、苏轼、米芾、赵孟頫、倪云林、吴镇,董其昌至齐白石等等这些中国艺术史上的巨匠,他们的作品与思想都贯穿或者说是支撑着整个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甚至某种程度上讲,文人画的发展史就是中国绘画艺术的思想发展史。文人画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艺术形态,表现在其独特的人格个性化、独立的人本;以及诗、书、画、印一体的精神化文本。这在国际上的独特性使得西方美术界认为文人画就是中国画,文人画艺术就是中国画艺术。如今,中西方艺术在多个领域跨界相融合,在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有如此高涨的趋势,此刻以民族艺术面貌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是当下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对文人画艺术不得不重新思考,不得不重新审视。
首先,需要重新认知的是文人画的定义,“文人画”并非“文人的画”。文人此概念,来源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古代教育并未普及,识字的人还很少,仅有的几名识字者为大家代读书信、代写文字等,他们这个群体是少数的另类群体,是不同于一般劳苦工作的农业劳动者,他们更多的是舞文弄墨和吟诗作画,考取功名。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普及,这群仅以文字和知识享有特权的文人群体已经被消解。所以文人这个特有的概念也逐渐消失。所以文人的画,并非文人画。真正的“文人画”是一个特定的艺术概念,甚至是一个特定的艺术审美观、或特定的艺术思想观。
在早期,并没有中国画的概念,仅有“画工”的概念只是一种职业同泥匠、木匠、瓦匠等属于一类。那时期修建寺院、陵墓,画工的工作就是绘制壁画,大量的画工中的高手成为了画手,而其中最优秀、最突出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称之为画师。画师的概念是最早的画家雏形。比如说“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的吴家样、曹家样等。后来这个等级的画师进入了宫廷,为皇家做工,他们隶属于宫廷,为皇家服务,依然不能表现自己,此时仍然是画工的属性。而当文人画思想的出现,这一切都有了重大改变。现在所认为的文人画鼻祖是王维。认为他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对于绘画和文学的相融,王维做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高度,但因此来说是文人画的发源,还不完全合适。因为当时的宫廷画师也同样将文学或诗学带进绘画,带入视觉性语言中。这都是为了取悦皇家,为了对于绘画的功能性作更高的拓展。此时文人画最核心的艺术观念还未形成。包括郭熙在内,他具有相当高超的画技,也具备极高的文学素养,但是他画的作品仍是为了“以画事君”,重点仍然是表达客观对象的真实性或赏玩性。并没有出现绘画作者本人的个性和独立的精神思想性。他们的画并非表达独立的自我。我们称之为院体画。这里就可以感觉到院体画同文人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艺术主张。
院体画是供人欣赏的,有观众和画者之分。文人画是自我心灵的抒发,观众和画者均为一人,即为自我心灵所绘。表现的是自我内心的世界。文人画的出现首先是观念性的改变,导致一种新的艺术思想地形成,比如苏轼、文同、米芾等。苏轼喜画枯木顽石,都是他个人“心中盘郁”的表现;文同说“吾乃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与墨竹······”这些画者对于枯木、顽石、墨竹并非执意,而是仅以此作为排解心中郁结,“意中所不适”,而书写。更注重的是自我心灵的感受,与外界事物拉开了所谓主客、彼此之间的差别。苏轼的那句“论画贵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若以形似来论画之高下,这种见地如同幼稚的孩子一般。这句话可以说是文人画崛起的标志,是文人画最早的精神内核。他强调心性,反对客观形似至上的标准。是一种全新的审美理论。他力图把画者从“画客观”,“画他者”中解放出来,将画中对象化的东西完全打破,直击画者本身独立的自我。这一点是文人画不同于院体画的关键。这句话也对文人画的确立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苏轼的论述,为当时文人画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当时并没有“文人画”这一概念,从宋到元,主导整个时代审美的还是院体画。院体画从晋唐以来的数百年,已经形成一整套完备的艺术审美标准和艺术技法规则,对于此时出现的一批看似笔墨松散、似是而非的简括作品,已是对主流审美进行了挑战。必然人们排挤这种新生的审美、对于他们的作品被认为是近似于笔墨游戏的“墨戏”,是文人士大夫的业余水平。所以文人画虽然在悄悄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体系,但是总体上仍然不被认可。直到被异族统治下的元代开始,历史的因素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皇家画院被撤除,画师们都走向了民间,院体画的力量逐渐消散,随之而来的是文人画的力量逐渐壮大。此时除历史因素之外,另一重要的原因——“纸”的出现,让笔墨的书写变得更加的自由,相比较于之前的绢本来看,提供了更大的技法空间,和更多的笔墨偶然效果。宣纸的渗水特性,完全不同于绢,所以之前建立在绢本作画技术体系被打破,纸本作品对墨和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提升,更适合于文人画所表达的那种复杂多样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无限的新奇水墨效果,为笔墨的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宣纸渗水的特性,也符合“不求形似”“直抒胸意”的文人画特点。此时期赵孟頫提出的“书画同源”更为文人画家将已有的个性成熟的书法形式融入到绘画中去,丰富了绘笔的情致,与内涵。元四家当中,王蒙、倪瓒、吴镇、黄公望,四人全是文人画家。也证明在元代,文人画从边缘走向主流,从萌芽走向成熟。文人画的形式表现在诗、书、画、印一体化,当时的文人画家自身本就擅长与书法和诗文,将书法和诗文与绘画共同结合,结合红色印章,将文学美、绘画美、书法美和印章美全部融为一体,并非简单的加法,而是成倍的提升了绘画内在艺术魅力。由此在元代中国文人特有的文化艺术形态被建立了起来。
进入明代,文人画开始经历一个复杂多变的进程,在明代早期,明太祖恢复了宋代宫廷画院体制,还设立了侍诏、副使、锦衣镇扶、供室内庭等十几个职位。院体画风重现盛世,“浙派”应运而生,文人画势头有所降落。直到成化年内,随着经济繁荣和城市的兴起,以文征明、沈周、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和后来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给文人画的发展带来了推动性作用。这里要特别指出,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将中国画分为南北两个派别,并依照禅学的顿悟和渐悟,称之为南宗和北宗。他褒南宗而抑北宗。被他划入南宗的画家有:王维、苏轼、元四家、文征明、沈周等。他对绘画本质的观念十分符合文人画。在《画禅室随笔》中他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以画为寄”、“寄乐于画”等,当时在他的身边聚集着一大批重要的士大夫和文人画家,所以他的思想对文人画的发展以及后来中国绘画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但是他提出的“师古”一说,影响到了后来中国画发展到“四王”阶段,已经进入了复古主义的泥潭,这是一个弊端。当然在此期间的徐渭、八大山人、石涛又让文人画发展出现了一个个耀眼的闪光点,八大山人就代表着文人画发展的高峰。他的画直抒心灵,与苏轼、倪瓒,成为文人画的主线。
随着时代变化,影响画坛的诸多因素变得复杂起来。外来艺术进入中国,同时书画市场的加速发展为画坛带来了巨大影响。后来的“扬州八怪”和“海上画派”均是此时其崛起的代表。比如海派的作品已经受市场影响具备了一定的“卖相”,这将徐渭、八大山人以来的大写意发展逐渐具有世俗化倾向。学术届依旧认为海派属于文人画,但其实此时的文人画已经失去了土壤,失去了文人画的核心思想,诗书画印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内容和本质上的精神已经改变。直到1921年,陈师曾发表《文人画价值》一文,又翻译日本大村西崖的《文人画复兴》一文,重新为文人画下了明确定义,清晰指出“文人画要表现独立精神、个人思想与情感、展现个性之美”。大村西崖的文中提到:“吾人之技巧与自然相肉搏,与造化血战,正如螳臂当车,蜉蝣撼树。盖无论如何,以自己之美,固不胜其任可知也。”“美术绝不以此无谓之望,欲与自然肉搏、驰骛者也。超越照相法之分野,独标高枝帜,得自立之本领者,在彼不在此也。”大村西崖在陈述自然万物不可描绘的局限性之后,提出“以自己之美,故胜其任可知也,”和“得自立之本领者”的观点,这均是直击文人画家自我反观、抒写自我心性的特质。
当然,文人画所带来的局限必然是有的,比如一些文人画表现的又出世清高的情绪、或寂寥的独自感受、也或是愤世嫉俗的孤傲等等,这些让文人画的概念蒙上了一层神秘和忧郁,以及不问世事的清冷。但本文所讨论的文人画精神价值,并不可淹没在部分文人画家的消极情绪中。文人画的丰富和多样性依旧会因不同的文人画家的个体区别和个性差异而建立。他们在对待艺术根本观念上的转变使得“文人画”在今天依旧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若仅以“消极”来判定文人画,也将“见于儿童邻”。大村西崖对此问题说的较为深刻:“虽觉寂寞,至艺术之本质,可谓充实而有光辉。”此处的艺术之本质参考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即:“艺术的任务,恐怕还是表现心灵吧!”